性的自由:允许跨性别儿童改变身体的道德理由 #
Chu, Andrea Long. “The Right to Change Sex.” Intelligencer, 11 Mar. 2024,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trans-rights-biological-sex-gender-judith-butler.html.
作者:朱华敏(Andrea Long Chu)
翻译:那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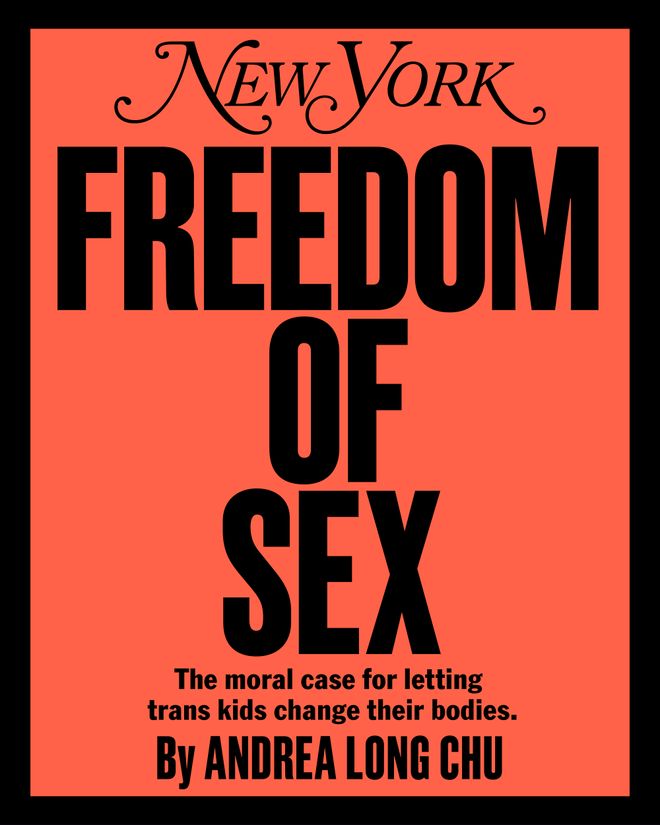
1 #
如今,人们经常听到性别(gender)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说法。这一想法有时要归功于《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一书,由年轻帅气的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于1990年所出版。事实上,早在 1960 年代,社会学家就已经开始将性别(gender)视作一种社会成就与性(sex)区分开来。巴特勒提出的观点更为激进:被反复引用的性别(gender)规范——比如穿高跟鞋或喝苏格兰威士忌——产生了一种对于生物性别(biological sex)的幻想,正等待着被填满意义。 在巴特勒看来,性别(gender)是表演性(performative)的,这个词是从语言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指的是那些像是在做某些事情的句子: 例如,「我保证」就是一个字面意义上做出承诺的短语。性别在这种意义上也是某种承诺——例如,「这是个女孩」——因为其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所以必须通过表演性的行为不断重申,并进一步允许了主流规范被重新协商甚至颠覆。巴特勒以变装表演中对正常性别规则的夸大为例,寓意每个人每天都在表演性别。
这些观点 对性别研究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针对巴特勒也很快出现了两个主要批评。首先,这些观点实际上否认了生理性别的真实性;毕竟,变装皇后和你们那些普通女性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第二,巴特勒把性别(gender)说得像是人可以主动选择的东西。巴特勒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努力承认性(sex)的物质性——即使Ta淡化了这一点的相关性——同时抵制性别(gender)可以被自发的意愿随意设定的观点。Ta写道,一个人并不是「早上醒来,在衣柜或更开阔的地方寻找要选择的性别,穿上这个性别过一天,然后在晚上放回原处。」
巴特勒始料未及的是,差不多 30 年后,人们真的会在早上醒来然后选择他们的新性别。至少这是人们从这个国家目前正激烈进行的关于青少年跨性别权利的「辩论」中得到的印象——这场迅速加速的运动联合了极右翼、中间自由派和某些左翼的女权主义者。去年作为至今最糟糕的一年中,共和党人提出了数百项法案,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性别肯定的医疗服务,限制跨性别儿童参加体育运动,并强迫学校将学生的情况告知家长。(并 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转向成年人)在所有跨性别青少年中,差不多有一半——约 14 万名儿童和青少年——现在生活的州中 未成年人已失去,或可能即将失去获得合法性别确认医疗的渠道。他们该向谁求助呢?纽约时报定期刊登报道,大肆渲染青少年性别医疗的危害;《哈利·波特》的作者 焦虑地将自己对性侵犯的恐惧从大洋彼岸投射到他们身上。公众越来越相信,孩子们所说的性别问题不过是一种烦恼:抑郁、焦虑、孤独症、家庭功能失调、同龄人压力,或是社交媒体;其中任何一种——更不用说青春期本身的普遍尴尬——都能更好地解释孩子对自己性别认同的怀疑。
左派必须考虑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左翼将跨性别权利挂在「性别认同」这一脆弱的钉子上,这个概念笨拙地从精神病学(对性别的病理化认识)的研究中改编而来,并受到性别研究和争取婚姻平等运动中(将性别认同和性向认同描述为)「生来如此」的策略的强烈影响。这使我们在社会接受度方面略有收获。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能形成一个连贯的道德解释,说明为什么某人的性别认同应该成为实际(作为性别肯定护理一部分)的生物学干预的理由。批评者问,如果性别(gender)真的是涵盖了一切的社会规范,并因此生产出性(sex)这一概念的错觉,那么为什么对某人性别认同的肯定必须要导致其生物学上的改变呢? 因此, 倡导者们又回到了 “性别不安 “的临床诊断上,这一诊断在大约十年前被称为 “性别认同障碍”,其定义是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与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不一致时所感受到的痛苦。长期以来,精神科医生一直用「跨性别者都在本质上患有精神疾病」这一观点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接受与性别过渡相关的治疗。通过 坚持这一诊断在医学上的有效性,进步人士将(关于跨性别医疗的)正义问题简化为谁患有适当疾病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为反对跨性别运动提供了系统性病理化跨性别儿童这一有力策略。
如何回应这一切?巴特勒的新书《 谁害怕性别》(Who’s Afraid of Gender?)就是一种尝试,它有望在本月晚些时候出版时,引发新一轮关于变性权利的公共讨论。Ta很好地描绘了全球范围内对「性别意识形态」的恐慌,并承认性别表演理论在随后的批评中似乎「值得商榷」。但Ta仍然认为性别(gender)是政治斗争中更有希望的领域。有人怀疑,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巴特勒仍然对性(sex)感到害怕。Ta并不孤单:许多跨性别权益的倡导者担心,如果他们 承认生理性别的重要性——就像反对者要求他们做的那样—就会削弱他们的政治诉求。鉴于性别(gender)所包含的大量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这方面的关注似乎可以为(性别的)自主决定提供更可信的基础。但这种担心为反对跨性别运动留下了大片政治领地。现在,反跨运动将其目标隐藏在中立客观的生物学事实背后。
在我看来,我们无法再承受更多恐惧的代价。正视生理性别的现实,顾名思义,并不是对这一现实宣誓效忠;没有人比希望改变自己生理性别的孩子更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明确、直接地捍卫这种愿望,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不再依赖性别(gender)这一观念。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学家曾假设,在自由社会中,性别角色的逐渐消失将导致希望改变生理性别的人数减少。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在性别(gender)的自由度提高的同时,希望改变生理性别的人数却在增加。对这些人来说,生理性别本身正在成为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并非前所未有: 许多美国人,尽管他们可能从未意识到,已经享受到了有限的改变性别生理的自由。新颖之处在于,这种自由可以被像年轻人这样在政治上被剥夺公民权的群体主张为一项普遍权利。这就是反对跨性别运动如此躁动的原因:它害怕性(sex)会成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十年前,当时代周刊令人难忘地宣布「 跨性别的转折点 」到来时,公众还朦朦胧胧地准备像对同性恋者那样接受跨性别者——安全、合法、罕见。2016 年,企业成功抵制了北卡罗来纳州限制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厕所的法律,这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就连候选人 特朗普也认为卫生间法案是一个失败的议题。然而,这个国家最初的那一阵充满责任感的宽容已经迅速消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注的焦点已经从成人转向了儿童。2018 年,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了记者杰西·辛格(Jesse Singal)的长篇封面故事「 当孩子们说他们是跨性别(When Children Say They’re Trans)」,聚焦了医学在对怀疑自身性别的青少年上产生的分歧。这篇报道为之后的报道提供了一个模板。首先,它把一个有可能成为社会问题(权利问题)的问题重新变成了一个医学问题(证据问题);然后,它悄悄地暗示,既然证据是有争议的,那么权利也是有争议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 在跨性别问题上,政治中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 最高法院 2020 年在博斯托克诉克莱顿县案(Bostock v. Clayton County)中的裁决,公众现在更 赞成保护跨性别者在就业、住房和公共空间免受歧视。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开始 认为性别(gender)是由出生时的性别(sex)决定的,甚至有更多人(近 70%)反对为跨性别儿童使用青春期阻断剂。

当今美国的反对跨性别集团主要有三种倾向。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一种,是宗教右翼,主要是基督教运动,他们认为跨性别者是可憎的,「性别意识形态」是左派使年轻人堕落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第二种倾向也很明显,但规模较小: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排跨激女(TERF)。这个群体起源于 70 年代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如今,这个原本代表「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这一辩论观点的缩写,被用来描述任何通过妇女权利为其反对跨性别观点辩护的女权主义者。这些观点包括:性别必须被粉碎,而不是被肯定;女性因其共同的生物学特征而构成「性别阶级」;跨性别权利的框架使原生女性暴露于跨性别女性的性暴力威胁下,而跨性别女性则被想象成掠夺性的男性。(美国的大多数 TERFism 都是舶来品: TERF 在英国的势力最为强大)。
但是,这个国家的反对跨性别运动最隐蔽的源头其实是自由派。巴特勒在对政治格局的调查中完全忽略了自由派。我怀疑这是因为,反对跨性别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表达担忧的公民,而不是在坚持某种意识形态。他既不是激进分子,也不是女权主义者;与其说他排斥跨性别,不如说他对所有社会正义运动都持广泛怀疑态度。他是一个跨性别不可知论的反动自由主义者 (trans-agnostic reactionary liberal)——TARL。根据这些人的说法,TARL 最关心的是 保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不受的 反自由主义的觉醒(woke)左派的影响,觉醒左派将性别正统观念强加于公众的喉咙,并恶毒攻击任何胆敢怀疑的人,他们贩卖的是审查、恐吓和类似宗教狂热。对于跨性别者本身,TARL 声称自己不持任何立场,只是对任何遭受心理困扰或公民权利受到侵犯的人 表示普遍同情。
在美国,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是《纽约时报(Times)》。在过去的几年里,该报大力宣传这样一种观点:就跨性别儿童的权利展开持续的公开辩论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紧迫的。仅在 2022 年,该报就用了超过 2.8 万字的篇幅来讨论跨性别青少年的话题,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杂志撰稿人Emily Bazelon撰写的长篇文章《 跨性别认同的青少年人数的不明增长(Unexplained Rise in Trans-Identified Teenagers)》。该报描绘了一幅完整的图景。该报记者认为,真正的跨性别者是临床上极少数患有经证实的精神疾病的成年人,他们的持续困扰使他们有权获得性别肯定医疗,如激素疗法和性别过渡相关的手术。我们被告知,跨性别青少年的人数「 虽然不多,但在不断增加」,他们被抑郁症或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疾病的合并症状所困扰,这些疾病阻碍了明确诊断,但他们却被匆忙地接受改变生活的治疗,其中许多人日后可能会后悔,这一点可以从那些 日后放弃性别过渡的人的警示故事中得到证明。更糟糕的是,右翼势力的反弹和跨性别活动家的激进策略激起了「过热的政治时刻」。这阻碍了医学界达成清醒的共识,而医学界通常被我们所信任。
与此同时,该报始终拒绝像对待其他医疗问题一样对待与性别过渡相关的医疗服务。去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 密苏里州一家小型性别诊所因「需求不断激增」而不堪重负的报道。但该报并没有像对待 全国范围内廉价家庭护理服务短缺,或多布斯案[ 1]后 外州病人涌入堕胎诊所那样,将其作为一个医疗资源问题来报道。相反,需求本身是可疑的,是一些难以解释的心理和社会力量的结果,这些力量让专家们「感到困惑」,而专家们的警告却一如既往地被激进分子的声音所淹没。事实上,阅读纽约时报的一般自由主义者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政治在阻碍建立科学共识的缓慢进程,因此跨性别者获得医疗服务的最佳机会就是不再对这些提出诉求。
纽约时报并非孤军奋战,它是《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等众多值得尊敬的刊物之一,在 媒体领域较为反动的角落里,这些刊物都参与了对 TARLs 所宣扬的观点的美化工作。其中参与的记者有辛格尔(Singal)、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马特·塔伊比(Matt Taibbi)、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梅根·道姆(Meghan Daum)等人,当然还有前时报工作人员巴里·魏斯(Bari Weiss)。这些作者中的许多人都在在线新闻平台 Substack 上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在那里,他们将自己描绘为勇敢的幸存者,声称被「觉醒(woke)」文化的精英阶层所「取消」。但他们绝非边缘力量。(正是魏斯的媒体公司 首先报道了密苏里州诊所的故事)。这些作者比他们在纽约时报的同行相比更加好战;他们尤其关注激进分子的「科学否认」行为,这些激进分子将「觉醒」置于理性的医疗标准之前。用一位 TARL 的话说,「生物学被取消了」。辛格尔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他经常指责跨性别积极分子发起了一场奥威尔式[ 2]的运动,否定「 生理性别的相关性」。他去年写道,如果一个 像他自己一样的「大块头男性」突然要求别人把他看成一个女人,那将是「极不公平的」。(他没有想到,这正是那些非常清楚自己生物学特性的跨性别女孩要求使用青春期阻断剂的原因:这样她们就不会长成杰西·辛格尔的样子)。
跨性别怀疑论者咬住了「 速发性别焦虑症(rapid-onset gender dysphoria)」这一概念不放。这是由公共卫生研究人员丽莎·利特曼(Lisa Littman)于2018年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没有性别不一致史的儿童由于「社会影响和适应不良的应对机制」而突然出现性别烦躁。这项研究是个骗局。它调查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而且还是从 网上跨性别怀疑论者的社区招募来的,它假定跨性别儿童的聚集产生是社会传染的证明,而不是比如说自我选择。 这种认为儿童受到互联网不当影响的观点,在从某个私人 Facebook 群组中招募的参与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无论如何,跨性别儿童的诊断结果是误导性的,并且后悔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症状会自然消退),这两个观点还是在反对跨性别运动中广为流传。
现在,要明确的是,TARL 通常会承认一群发育完全的成年人的存在,他们经医学验证的性别烦躁是如此顽固和令人痛苦,以至于支持同情关怀的理由超过了希波克拉底禁止伤害一个完全健康的身体的规定。这里的核心策略是制作一种入院表格,上面正好有两个方框。每一个自称跨性别的人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以受医学承认的方式疯了(两个方框可以同时打勾)。这种方法颇有天才的意味。它在说自己是跨性别者的孩子和真正是跨性别者的孩子之间划出了明确界限,同时将他们全部病理化:要么是妄想症,要么是性别烦躁。 这条界限与性别医学本身一样古老,几十年来,性别医学一直小心翼翼地将假冒者、恋物癖与「真正的跨性别」区分开来。因此,在大多数性别不一致的案例中,TARL 会告诉家长, 男孩穿裙子和女孩爬树都是非常健康的,无论他们的生理性别如何,都不需要改变。他向家长们保证,那些自称跨性别的青少年的自杀风险 被愤世嫉俗的激进分子夸大了,以试图来要挟公众;他的意思是,他不认为大多数孩子的自杀倾向强烈到足以使他们(不得不)成为跨性别。 对于那些极少数真正的悲惨事件,他建议采取「 观察等待」的做法,宁愿让患者经历青春期到成年期往往不可逆转的变化,届时她童年的性别不协调经历将最终获得医学证据的支持:如果她能早点说出来这些就好了!
这显然不是对正义的构想,而是对流行病的应对计划。我们并不需要感到惊讶。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许多人认为,跨性别者是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会想要成为的人。 反对跨性别阵营一般都把目标对准儿童,因为美国人倾向于把儿童想象成纯洁无暇的人性的源泉,也把他们想象成无知且没有理性思维或政治能动性的依附者。这使得该运动不仅将儿童,而且将所有跨性别者都低龄化了,只想带领他们从精神疾病的摧残和年轻人的鲁莽中走出来。如果在混杂的反对跨性别集团中一个自由主义的怀疑论者不会声称跨性别者的数量应该减少,那么他仍然期待我们在基本的人道主义基础上认同,至少不应该有更多的跨性别者。 例如,我们可以认为,癌症病人应该有条件接受存在彻底改变他们人生风险的积极治疗,同时也真诚地相信,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没有人会得癌症。
除非我们纯粹从跨性别儿童自身的角度来理解他们:他们是希望改变生理性别(sex)的社会正式成员,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捍卫跨性别儿童的权利。这种愿望从何而来并不重要。当 TARL 反复暗示跨性别青少年的突然增加是「无法解释的」时,他试图诱使我们认为跨性别权利实际上在一个好的解释的另一面。但是,任何关于跨性别者「从何而来」的模式——无一例外——都会在一般情况下质疑任何不符合其病因特征的个体所接受的医疗照顾。这既适用于旧的精神病学假说,即跨性存在(transsexuality)是 子宫内接触母体性激素的结果,也适用于善意但被误导的 那些试图寻找「导致」性别不一致的基因的研究。正如 LGBTQ+ 倡导者喜欢说的那样,目前的性别认同模式是 「 一致的、坚决的和持久的」,这无疑也是正确的。这些理论最多只能让我们在试图取消合法地位的持续攻击中获得短暂的喘息,但它们永远无法拯救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好捍卫这样一个观点:原则上,每个人都应该能获得变性医疗服务(sex-changing medical care),无论其年龄、性别认同、社会环境或精神病史如何。 这可能会让你感觉是一项令人头晕目眩的任务。好消息是,数百万人已经相信了这一点。
2 #
1958 年 10 月,一位年轻女性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系,她的主诉与众不同。艾格尼丝(Agnes),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那位,胸部丰满,皮肤光滑,腰身纤细。但她也同样有着,令她男友无比惊愕的,一副典型的男性生殖器。在接受精神病学家罗伯特·J·斯托勒(Robert J. Stoller)的采访时,艾格尼丝提及了她是如何被当作男孩抚养长大的,但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一想法在她青春期时得到了证实:她自然而然地开始发育乳房。检测结果表明,艾格尼丝没有子宫或卵巢,但她的睾丸会产生高水平的雌激素。医生满意地通过手术将她的生殖器换成了由阴茎和阴囊组织构成的阴道。斯托勒非常喜欢艾格尼丝,因为她为他的理论提供了证据,即内分泌系统对一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识到自己的生理性别具有很强的决定性作用(他和他在洛杉矶的同事将此称为「性别认同」)。多年后,艾格尼丝随意地说出了真相:12 岁时,她被完全典型的男性青春期的到来所困扰,开始服用母亲的雌激素药片。 斯托勒在他 1967 年《性与性别》(Sex and Gender)一书中承认:「她并不像我报道的那样,是’生物力量’微妙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性别认同的案例。」「她是一个跨性(者)」。
艾格尼丝简单地 告诉了医生他们想听的话。但她的母亲为什么一开始会有雌激素药片呢?斯托勒顺带着指出,后者在做了包括卵巢在内的全子宫切除术后,医生给她开了一种合成雌激素;换句话说,她是在 20 世纪数百万被提供雌激素来治疗更年期症状的女性之一。妇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A. Wilson)在其 1966 年的畅销书《女性永恒(Feminine Forever)》中认为,更年期总的来说是一种激素缺乏症,就像糖尿病一样,可以通过雌激素疗法安全地治疗。他声称,他的病人是新的性革命的一部分:她们拥有柔软的乳房、光滑的皮肤和穿着网球裙也很好看的双腿。威尔逊死后,人们发现他一直在接受 普瑞马林[3]制造商的贿赂。尽管如此,许多妇女确实发现激素疗法对从潮热到阴道萎缩等各种更年期症状有效,直到1992 年,普瑞马林成为了 美国处方量最大的药物。「女人毕竟有权继续做女人,」威尔逊曾这样写道,「她们不应该后半辈子都过着中性的生活。」
因此,当艾格尼丝访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她并不需要证明存在自己有着属于女性生物学的权利。她只是想让医生相信,这项权利也适用于她。 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人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保持自己的生理性别。被强行变性的可能性是恐怖电影的素材。1997 年,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一个匿名男子的故事,后来被确认为大卫·雷默(David Reimer)。他 在一次拙劣的割礼手术后被当作女孩养大。他的治疗由斯托勒的同事、备受争议的心理学家约翰·莫尼(John Money)负责。莫尼给雷默提供雌激素以诱导他的乳房发育,并据称还让他与双胞胎兄弟进行性行为。在青少年时期得知真相后,雷默开始服用睾酮激素,切除了乳房,并接受了阴茎整形手术。这只是一个在这个国家发生的小小的悲剧,不值一提。纽约时报却将他的挣扎比作 俄狄浦斯或李尔王的苦难;2004 年他自杀时,该报还 刊登了他的讣告。雷默的故事在反对跨性别文本中很受欢迎,因为除了这个事件所代表的普遍堕落之外,它似乎还证明了性别(gender)在生理性别中有着不可避免的基础:雷默知道他从不是女孩,不管医生对他做了什么。他 告诉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他从来没有适应过女孩的生活,喜欢爬树和玩卡车,即使他的母亲试图说服他,他只是一个「假小子」。
当然,这正是如今许多跨性别儿童与父母的对话。雷默的故事实际上说明,当我们把改变性别理解为变回原来的性别时,我们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一进程的。 这种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经常发生。历史学家朱尔斯·吉尔-彼得森(Jules Gill-Peterson)指出,性别医学领域最早的治疗方法是为了「矫正」间性的儿童,将他们模糊的生物学特征纳入社会认为正常的范围。即使后来这些治疗方法被谨慎地推广到「跨性者」身上,也往往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这些人身上某些原本的生物性别,也许是本质上的内分泌系统,正在被挖掘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斯托勒对艾格尼丝的睾丸产生了如此多的雌激素感到如此兴奋)。但是,随着医学对性(sex)的理解逐渐增加,这一概念也包括了性腺发育和激素活动等方面,并且还关注到了由于年龄、遗传、疾病、身体创伤或医疗副作用而丧失性别的风险。这就是艾格尼丝的计划的巧妙之处。她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像她母亲一样需要变回女性的人。事实上,在摘除睾丸后,她擅自停用了她的秘密雌激素药片,导致情绪波动和潮热。医生立即诊断她患上了——还有什么?——更年期综合征,并让她接受了与数百万人同样的雌激素疗法相同的治疗。
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别(gender)承认医疗,是更广泛的性(sex)承认医疗历史的一部分,它受健康、生产力和道德价值等强大的规范性观念的支配。 这一领域的许多治疗方法如今已经都没有争议:癌症后的乳房重建、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血管扩张剂、治疗脱发和多毛症的抗雄激素。2023 年,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对 更年期激素疗法 「使人安心」的证据基础表示同情,作者称这种疗法「失去的改善妇女生活的机会」。几年前,纽约时报为首次成功移植阴茎、阴囊和周围腹壁而欢呼——这是一项由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的成果,目的是让 生殖器被简易爆炸装置损伤或摧毁的士兵恢复尊严。 (捐赠者的家人给病人发了一条信息:「我们都为我们的所爱之人能够帮助到一位为国效力的年轻人而感到自豪。」) 即使是 最近阿拉巴马州共和党急于将由于州最高法院的一项意外裁决而濒临危险的试管婴儿治疗的合法性写入法律,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即许多宗教保守份子实际上支持对生物性别进行重大医疗干预——通过促性腺激素刺激卵泡生成,并且用 GnRH 促效剂防止卵子意外排出,更不用说试管的整个过程——只要回报是一个人类婴儿。
真正的问题是,哪种性别(sex)可以被确认——以及为什么。 举例来说,用于生育治疗的 GnRH 促效剂 也被用于推迟跨性别儿童的青春期。这意味着,你们一般的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现在会在表面上认为, 给孩子服用与他母亲怀上他时使用的激素阻断剂一样的药物,应该是一项重罪。我们的政客可能会理直气壮地抗议说,这是将同一种药物用于截然不同的目的。但问题是:这里决定性别转变是否被接受的是转变的目的,而不是转变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性别承认医疗在历史上既需要阻止一些人进行性别转变,又需要对另一些人实施性别转变。与大多数医学领域一样,它的背后也有血腥的胁迫:19 世纪 40 年代阿拉巴马州 对被奴役的女性进行的阴道手术试验;纳粹德国对男同性恋者进行的睾丸移植手术;以及至今仍在继续的 对非典型生殖器婴儿的手术改造。甚至连威尔逊也明显专注于让女性为丈夫保持活泼和润滑。 在《女性永恒(Feminine Forever)》一书中,他幽默地回忆起一个男人把 0.32 自动手枪放在桌子上,然后声称如果医生不能「治愈」他妻子凶恶的性格,他一定会亲手杀了她。
3 #
大多数人并不是在枪口下被迫改变性别(sex)的。但现在应当明确的是,当反对跨性别运动的成员辩称性别(sex)不能改变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为了符合社会规范,那么性别就不能改变。 巴特勒在这方面写过很多内容;一个有力的规范理论可以说是他们毕生的心血。对于巴特勒来说,社会规范不是一种信仰或文化态度。它是一种深层次的权力结构,使人对自我的感知得以可能。规范先于我们,形成我们,并充当我们的「构成性限制」;同时,由于规范依赖于不断地被重新强调,它们永远不会完全地捕获我们,并总是可以被重新诠释。(Ta 把这个称作「发掘规范之中的弱点」)巴特勒倾向于从意义的角度来思考性别规范;事实上,Ta 经常假定性别(gender)本身是一种符号结构,只有在这种结构中,性(sex)才变得重要。 这也是 Ta 更广泛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通过证明某个事物充满了社会层面的意义,使其在政治层面上显得可疑。
但仅仅知道性(sex)的含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了解它的作用。显然,性别规范并不是直接从器官中产生的。我们可以想象,即使在切除子宫后,艾格尼丝的母亲仍被期望具有养育子女的能力和情感。然而,如果只谈论规范,就会忽视生理性别在更大的物质关系的系统中的作用。 如果不是因为繁衍后代这一事实,我们很难解释上述的性别规范为何一开始会存在,因为人类的生殖仍然需要非常特殊的生物条件才能得以发生,包括至少一个的每种配子类型(精子和卵子)、功能良好的子宫和合理健康的内分泌系统。这就是作为生物能力的性;在这种意义上,性作为一种物质资源不亚于水或小麦。每一个致力于延续自身的人类社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类社会——都规定了生物性别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这不仅仅是基于性的劳动分工(类似猎人-采集者之类的工作)。这是真正的关于性的分工。
这听起来好像是我在说性比性别更加真实——这是一个性别研究自诞生以来就对这一命题深恶痛绝。我并不认为性比性别更真实。但是我也并不会对「性的分工决定了性别规范」这一说法感到太多困扰,只要我们记住,前者永远无法完全决定后者。 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不断变化的和无规律的差距。我们可以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找到一个残酷的例子。正如霍滕丝·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所写的那样,当白人奴隶主强奸被奴役的黑人妇女时,南方传统中那种有教养的绅士制度就被直接放弃了。这些妇女本来可以通过生育与自己断绝关系的孩子的方式来生产许多新的财富——也就是说,新的被奴役的人。性别(Gender)本身无法解释这种安排;它无法说明性(sex)是如何作为一种物质基础发挥作用的,就像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它是劳动、财富和权力的来源,并且精心安排的性别上层建筑则不断从其中出现、断裂,并且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被重新塑造。(这种结构被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于 1975 年起了一个老式的名字——性-性别系统(sex-gender system))。
这也难怪,所谓「性别认同」,作为一个被善意的 LGBTQ+ 倡导者一般理解为一种抽象感受的概念,在为性别转变做辩护方面做得如此糟糕。 如果生理性别是价值的物质结构的一部分,那么社会就会对任何可能产生的潜在收益或损失产生具体的兴趣,而不会关注感受。 吉尔-彼得森(Gill-Peterson)讲述了罗伯特·斯通斯特里特(Robert Stonestreet)的故事,1915 年,一个 10 岁的男孩因罕见的尿道缺陷被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当医生告诉他的父亲,这个男孩有卵巢,应该被重新指派为女孩时,他的父亲拒绝了,并解释说,他家里已经有六个女孩了,而他的儿子是家里农场的好帮手。当然,斯通斯特里特当时还未到青春期。无论他比他的姐姐们有什么生理优势,都是每天在农场劳作就自然会得到的。这里的重点在于,他父亲对他的性别(gender)的社会认可,总的来说只是对他的性别(sex)的经济考量的附带结果。 21 年后,斯通斯特里特要求当年的医生证明他是男性,以便他能与未婚妻结婚。他们拒绝了——有人怀疑,这是因为没有生育能力的婚姻让他们觉得是死路一条,尤其是在全国出生率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三天后,斯通斯特里特自杀——他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因为这个社会无法决定如何最好地解释他的性别(gender),同时又从他的性别(sex)中获取价值。
这就是反对跨性别运动不想跨性别者接受性别转变医疗的更大历史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如果可能的话,跨性别者将如何融入美国社会的性的分工。毕竟,TERF 并不害怕在女厕所里受到 Y 染色体的攻击。她们的偏执幻想是一个充满雄性激素的庞大身体挥舞着阴茎——这个器官,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那样,被 TERF 赋予了近乎魔法般的暴力力量。(TERF 们似乎经常以跨性别女性不足以被强奸为由,拒绝跨性别女性也是女性的观点,尽管事实上, 跨性别女性所面临的被性侵犯的风险要高得多)。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反对跨性别女孩参加体育运动,不是因为精子比卵子游得快,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跨性别女孩会比自己的小女儿游得快,并且 使她们获得体育奖学金或其他机会的权利被剥夺。甚至连辛格尔也承认,这最终是一个「 权利诉求之间的竞争」的问题,而不是基于生物学事实。 跨性别女孩在其选择的运动项目中总是占有优势,这种很大程度上是幻想的想法引起了广泛的不适。这反映了一种根本的父权制的信念,男性(male)的身体优势只要是被男人(men)所拥有,就完全可以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运动中基于性的分工是为了维护不平等,而不是为了缓解不平等)。
反对跨性别集团并不关心在某种不流血的、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性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性」能做什么——或者说,如果与性别过渡相关的医疗能够广泛普及,「性」将不再能够做什么。 反对跨性别运动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寻求医疗服务的跨性别儿童群体的变化,根据一些统计,这一群体现在主要是指派女性。(这一说法的准确性一直 存在争议。)这一观点在阿比盖尔·施里尔(Abigail Shrier)在 2020 年出版的作品《不可逆转的伤害:引诱我们的女儿堕落的跨性别狂热(Irreversible Damage: The Transgender Craze Seducing Our Daughters)》中得到了推广。 该书歇斯底里地声称,焦虑和抑郁的流行正在导致「一代女孩」将女性青春期的磨难与真正的性别不安混为一谈。施里尔写道,这种流行的代价是「一磅肉」,而她指的是哪一磅肉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本书的封面插图是一个女孩,在她本来子宫的位置有一个洞——你可以用手指穿过去。大规模不孕症的威胁不容低估。我毫不夸张地说,反对跨性别运动被一种深层次的、无意识的恐惧所驱动,即社会将没有足够可用的女性生物系统来支撑日益恶化的核心家庭——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基于性的分工本身。
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性别转变医疗确实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生育能力,但并不总是不可逆转的,而且跨性别群体数量仍然太少,以至于不可能带来那种人口大灾难。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种潜在的性分工的重新配置——这会让任何本能地忠于现状的人感到极度恐慌,但其中内在的革命性并不比,比如说,避孕药更多。 毕竟,避孕药是 20 世纪性别改变医疗领域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它对女性的性自由和经济独立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并没有带来妇女解放。恰恰相反,它成为了性分工内部的一个被称为「计划生育」的新制度的理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一个稍微仁慈一点的社会将激素疗法和青春期阻断剂纳入自己的性分工,而不会意外地废除家庭或粉碎父权制。真正的政治变革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实现。性别肯定医疗一直服务于某些人对社会的道德愿景。没有理由它不能为我们的社会服务。
4 #
「如果我们把自由变成我们共同呼吸的空气呢?」巴特勒在《谁害怕性别?(Who’s Afraid of Gender?)》的结尾这样问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想法。这并不意味着废除社会规范——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而是通过跨越我们的诸多差异结成的联盟,对社会规范进行集体再创造。 巴特勒认为,争取跨性别权利的斗争不能仅仅是文化上的,而必须与争取「住房、食物、无污染的环境、无法偿还的债务和医疗保健等基本权利」联系起来。Ta 说得完全正确。但 Ta 对建立联盟的原则性承诺,可能会使 Ta 走向不必要的和解立场。比如说,「跨性别者的性别自决权不会夺走其他任何人的权利」,这一点就很不明确。如果这意味着跨性别者可以获得社会承认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不会损害其他人对同样权利的要求,那么这在技术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性真的是一种生物资源,那么在没有实际物质损失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对性的分工进行重塑——这就好像说社会主义不会拿走富人的权利一样。 这就是巴特勒这样的社会分析的局限性。它把反对跨性别运动想象成主要由宗教狂热分子和诡计多端的政客组成,而没有考虑到,许多人可能会为了物质利益,反对我们理应呼唤的,对性的再分配。
我们需要更强烈的要求。巴特勒认为,将压迫性制度的存在归咎于生物学是「适得其反和错误的」。但为什么呢?我认为,任何全面的跨性别权利运动,都必须能够在生物学本身的层面上提出政治要求。 这是一个古老的激进女权主义观点,最著名的见于舒拉米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1970 年的经典著作《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费尔斯通写道,假设女性被压迫,真的是她们生物学结构的产物。然后呢?那便是,女权主义者必须努力改变生物学结构的现实。 这个开局的天才之处在于,它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生物学事实具有某种内在的道德价值,而社会或文化事实则没有。生物学无法为对人类的剥削所辩护;事实上,生物学甚至无法为生物学本身所辩护,因为生物学与任何社会一样能够使不公正永久化。 当费尔斯通将女性称为「性阶级」时,她——与追随她的 TERFs 不同——想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阶级社会的梦想,一个只有将人类从「生物学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的梦想。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一项「革命性的生态计划」,即生育控制、人工繁殖和劳动的全面自动化。这听起来可能不太现实。但这就是重点:正义总是试图改变现实。
性是真实的。全球变暖也是真实的。正如我们从气候行动主义中了解到的那样,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是对它们提出规范性主张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但是,我认为,仅仅因为现实是真实的,我们就有接受现实的道德义务,这是虚无主义的一个很好的定义。跨性别儿童想说的是:变性的权利——也就是那些一直都被他们的父母、朋友、老师、教练、医生和代表(尤其是白人和富裕阶层)几十年来所享有的权利——同样属于 Ta 们。 我们不应该把这项权利理解为对一个永远处于崩溃边缘的现有社会秩序的摒弃主义效忠,而是来自于更广泛的生物正义理想,其中还包括堕胎权、获得营养食品和清洁水的权利,以及至关重要的医疗保健权。
我这里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遍权利:性的自由(Freedom of Sex)。这种自由包括两项主要权利:在不诉诸性别(gender)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生理性别的权利,以及拥有不受生物学结构决定自身性别的权利。 一个人可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行使这两项权利——比如说性别过渡——但这两项权利都不能与另一项权利混为一谈。我想到了两院制。每个议院都有自己的特权,但无论是排他性的上院(性)还是喧闹的下院(性别),都没有否决对方的最终权力。(并非所有跨性别者都希望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有些跨性别者也是非常规性别)。通过主张性的自由,我们可以不再依赖于越来越形而上学的性别认同概念,来为性别改变医疗辩护,就好像只有当一个人的生理性别与刻在他灵魂上的序列号不一致时,这种护理才是被允许的。「出生时指派的性(sex assigned at birth」也是如此,它无益地掩盖了一种生物学进程,许多人实际上都有权改变这种进程。 总之,我们必须摒弃性与性别之间存在任何必然关系的观念;这使我们能够宣称,将性与性别以一个人选择的方式任意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这种自由在实践中是什么样的呢?让任何人改变Ta的性(sex)。让任何人改变Ta的性别(gender)。让任何人能够反复改变Ta的性(sex)。让跨性别女孩参加体育运动,无论其性别(sex)状况如何。如果她们表现出色,这只能说明有些女孩比其他女孩更擅长运动。让人们使用自己选择的性别(gender)隔离设施;在可能的时候取消隔离。不要给孩子向Ta的父母出柜。不要强迫任何人改变自己的性(sex)或者性别(gender)。为每个人提供医疗服务。反对跨性别运动收集了公众对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夸张的不公正的日益增长的意识,并将其像充满空气的注射器一样,对准了一小部分儿童群体。这样做的效果是让人觉得跨性别者好像不想要好的医疗服务或不想要值得信赖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而事实是跨性别者面临着全面的健康差异,包括 较高的残疾、哮喘和心脏病报告率。没有任何一项联邦计划能比「全民医保」更能惠及跨性别者了。至于与性别过渡相关的护理本身,变性(sex)的权利包括接受咨询、了解风险或接受治疗合并症的权利;事实上,社会有义务让跨性别儿童免费、广泛地获得这些资源。但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选择,而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将 「深思熟虑」作为任何普遍权利的要求,都是在将这种权利变为一种排他性的特权。 在大多数情况下,跨性别儿童获得护理的机会将经过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作为中介,这是我们的社会看待儿童的方式中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是否正确。目前,家长必须学会把他们的孩子以本来的方式来对待:能够享有自由的人。
性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幸福。它本来也不需要。这一点的倡导者对自由主义者所固执地强调的那些关于性别(sex)改变医疗的健康风险,和放弃性别过渡的潜在可能性进行反击是正确的。但是,有自由的地方就会有遗憾,这也是事实。事实上,没有自由就不会有遗憾。遗憾是被投射到过去的自由。因此,对决定的结果感到遗憾是一回事,但对决定的自由本身感到遗憾则是截然不同的事情,而大多数人都不会用决定的自由来避免可能的遗憾。如果我们要承认跨性别儿童的权利,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面对危险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向每一个看着足球的幼儿注射睾酮激素。但是,如果孩子们太小而无法为青春期阻断剂提供同意,那么他们肯定也太小而无法为青春期提供同意,因为青春期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生理动荡。 然而,我们每天都在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不乏受害者。我说的不是自杀;我说的是许多跨性别权利的反对者,他们惊恐地发现,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可能进行性别过渡, 因为他们如此强烈地憎恨自己是年轻女孩。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否仍会对自己的生物学身体感到后悔。但我确实怀疑他们后悔的是,他们从未有过选择的机会。
一种选择!一种不可能的想法。然而,我们不难相信,30 万跨性别儿童可以选择不再成为跨性别者。当自由只是依照你被告知的方式行事时,它便是很容易想象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是,他们为什么一开始要在性别问题上制造麻烦。 他们不欠我们一个解释。他们正忙于掌控自己的创造。他们可能不会改变世界,但一定会改变自己。「可能性,」巴特勒曾写道,「不是奢侈品,它就像面包一样至关重要。」我们还没有开始理解一个孩子在没有任何生物学「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第一次说自己是女孩的勇气。尤其是如果她生活的州正在努力确保像她这样的跨性别孩子只能这么说的时候。但无论如何,她还是说了。「我是一个女孩」这句话是经典意义上的表演性语言:它表演了一个动作。她不仅是在宣布自己将来要行使自己对于性的自由的意图,通过说出这句话,她已经在行使性自由了。 她是在利用规范中的弱点。她不是害怕性,而是反对性。这不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确实希望跨性别儿童存在。我听说他们人数不算多,但在不断增加。
——————
1 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是一起美国最高法院案件,针对2018年密西西比州禁止在怀孕15周后进行堕胎手术的法律的合宪性问题进行裁决。下级法院在临时禁止令中裁定阻止该法律的执行,理由是该法律违反了在计划生育联合会诉凯西案中所确立的允许女性在怀孕前24周自由选择堕胎的权利。该案的口头辩论于2021年12月举行。(Wikipedia)
2 “奥威尔主义”指现代专制政权借由严厉执行政治宣传、监视、故意提供虚假资料、否认事实(双重思想)和操纵过去(包括制造“非人”,意指把一个人过去的存在从公共记录和记忆中消除)的政策以控制社会。(Wikipedia)
3 Premarin,一种从怀孕母马尿液中提取的雌激素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