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政治学 #
Mbembe, Achille. Necro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作者:Achille Mbembe
译者:弱心海
原文链接
本文选自 Necropolitics 第三章同名章节。
主权(sovereignty)之最终体现主要在于决定谁能够_生_、谁必须_死_的权力与能力。 [2] 因此,杀戮或放生构成了主权之界限及其主要属性。主权就是对死亡施加控制,并将生命定义为权力之部署(deployment)和显露。
这就是米歇尔-福柯所说的 “生命权力(biopower)":权力控制的生命领域。 [3] 但是,在什么实际条件下行使杀人、放生或置于死地的权力?谁是这一权利的主体?这种权利之行使对被处死者以及将其与凶手对立起来的*敌意(enmity)*关系有何启示?生命权力的概念能否解释当代政治以战争、抵抗或反恐行动为幌子,将谋杀敌人作为其首要的、绝对的目标的方式?毕竟,战争既是实现主权的手段,也是行使杀戮权利的方式。当政治被视作战争的一种形式时,就需要问一问生、死和人体(尤其是受伤时或被杀时)的地位。这些方面是如何体现在权力秩序中的?
死亡劳动 #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借鉴了生命权力的概念,并探讨了这一概念与主权(统治权)以及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概念的关系。 [4] 我想简要探讨一下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一些经验与哲学问题。众所周知,例外状态的概念与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中营/灭绝营频繁地联系在一起讨论。对死亡集中营的颇多解释尤其将其视为主权与破坏性暴力的核心隐喻,以及消极力量绝对化的终极标志。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集中营的生活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它的恐怖永远无法被想象力所完全接受,原因就在于它游离于生死之外”。 [5] 在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看来,由于集中营的居民被剥夺了政治地位,沦为赤裸生命(bare life),因此集中营是 “地球上出现过的最绝对的非人条件得以实现的地方”。 [6] 他补充说,在集中营的政治-法权结构中,例外状态不再是法律状态之时间性中止**,而是获得了一种永久性的空间安排,持续处于法律之正常状态之外。

换言之,在区分理性与非理性(激情、幻想)的基础上,晚期现代批评得以阐明某种关于政治、社会、主体的观念,或者更根本的是,某种关于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美好生活以及如何在此过程中成为一个完全道德的主体的观念。在这一范式中,理乃是主体之真理,而政治则是在公共领域行使理性。理性之行使等同于自由之行使,是个人自自主的关键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主权之浪漫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主体既是其自身意义的主宰者,也是其自身意义的控制者。因此,主权被定义为自我规定与自我限制(为自己设定限制)的双重过程。反过来,行使主权即指社会借助受特定社会和想象符号所启发的制度进行自我创造的能力。 [7]
对主权政治的这种强烈的规范性解读已经提出了一些批评,我在此不再赘述。 [8] 我所关注的是那些主权(支配性)人物(figures of sovereignty),他们的核心项目不是为自治而斗争,而是将人之存在普遍工具化,并对人的身体和人口进行物质毁灭……这些主权人物绝非惊人的疯狂或失常(prodigious insanity),也不是身体冲动&利益或心灵冲动&利益之间断裂的表现。事实上,就像死亡集中营一样,这些形象构成了我们继续生活的政治空间的法则。此外,当代人类毁灭的经验表明,对政治、主权和主体的解读可能有别于现代性哲学话语留给我们的解读。与其将理性视为主体之真理,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其他不那么抽象的、更加具体的基础范畴,比如生与死。
黑格尔关于死亡与 “成为主体(becoming subject)"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此具有重要意义。他对死亡的论述以双重否定性概念为中心。首先,人对自然进行否定(这种否定在人将自然还原为人的需要的努力中被外化);其次,被否定的因素通过劳动和斗争被转化。通过改造自然,人类创造了一个世界,但在此过程中,人类也暴露出自身的否定性。在黑格尔的范式中,人之死亡本质上是自愿的。它是主体有意识地承担风险的结果。黑格尔认为,通过这些风险,构成人类主体自然存在的 *“动物 “*被打败了。
换言之,人因此真正成为了一个主体——即在对抗***死亡(被理解为否定性的暴力)***的斗争中以及劳动中,同动物分离。通过这种与死亡的对抗,人被抛入了历史之不息运动中。因此,要成为主体,就必须坚持死亡之劳动。坚持死亡之劳动,这恰是黑格尔对精神生活的定义。他说,精神的生命不是害怕死亡、免于毁灭的生命,而是承担死亡、与死亡共存的生命。精神只有在绝对的肢解中发现自己,才能获得真理。 [9] 因此,政治是活出人类生命的死亡。这也是绝对知识和绝对主权之定义: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冒险。
乔治-巴塔耶对死亡如何构建主权、政治和主体的概念也提出了批判性的见解。巴塔耶至少从三个方面取代了黑格尔关于死亡、主权和主体之间联系的概念。首先,他将死亡和主权解释为交换和超富足(superabundance)之阵痛,或者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过度(excess)。在巴塔耶看来,只有当死亡将生命作为人质时,生命才是有缺陷的。生命本身只存在于与死亡的交换中。 [10] 他认为,死亡乃生命之腐败,是生命之恶臭,既是生命的源泉,又是令人厌恶的条件。因此,尽管死亡摧毁了本应存在的东西,抹去了本应继续存在的东西,并使接受死亡的个体化为乌有,但死亡并不等于存在之纯粹毁灭。相反,死亡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意识;此外,死亡是生命最奢侈的形式,也就是生命之涌流和旺盛:一种增殖之力量。更为彻底的是,巴塔耶将死亡从意义的视野中减去。与此相反,在黑格尔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在死亡中彻底丧失;事实上,对他来说,死亡作为通向真理的一种手段,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巴塔耶在死亡、主权和性之间建立了关联。在他看来,性与暴力以及通过狂欢和排泄冲动消解身体和自我的界限密不可分。因此,性涉及人类冲动两极化的两种主要形式——排泄和占有——以及围绕它们的禁忌制度。 [11]性之真相及其致命的属性,就在于现实、事件和幻想对象之间失去界限的体验。
对巴塔耶来说,主权有多种形式。但归根结底,它是拒绝接受死亡之恐惧所要求主体尊重的限制(a refusal to accept the limits that the fear of death would have the subject respect)。巴塔耶认为,“主权世界 “是一个取消了死亡限制的世界。死亡存在于其中,其存在定义了这个暴力世界,但死亡存在的同时,它永远只是为了被否定而存在。他总结道:“他就是他,仿佛死亡并不….,他对身份的限制与对死亡的限制并不在意,或者说,这些限制是一样的;他是对所有这些限制的超越。"。由于禁止的自然领域包括死亡以及其他领域(如性、污秽和排泄物),主权需要 “违反禁止杀戮的禁令的力量,尽管这确实会在习俗所规定的条件下”。与植根于必要性和所谓避免死亡的需要的从属关系相反,主权绝对要求冒死亡的风险。 [12]
通过将主权视为对禁令的违反、僭越(violating),巴塔耶重新提出了政治之界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不是理性之辩证运动。它只能被追溯为一种螺旋式的僭越,追溯为使限制之概念本身失色的差异。更具体地说,它是因违反禁忌而产生的差异。 [13]
敌意关系 #
在介绍了作为死亡劳动的政治之后,我现在来谈谈主权,它被定义为杀人的权利。为了论证的目的,我将福柯的生命权力概念与另外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和戒严状态(也被译作“围困状态”)(the state of siege)。 [14]我研究了例外状态和敌意关系成为杀人权之规范基础的轨迹。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不一定是国家权力)不断提及和呼吁例外、紧急状态以及虚构的敌人概念。权力也在努力制造同样的例外、紧急情况和虚构的敌人。因此,问题就变成了:政治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那些仅通过紧急状态运作的制度中,政治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福柯的著作中,生命权力似乎是通过将人分为生者和死者来发挥作用的。由于这种权力是在生与死的分裂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它将自己定义为与生命领域相关的权力,它控制着生命领域,并将自己投入其中。这种控制之先决条件是将人类物种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将人口细分为不同的亚群体,并在这些亚群体之间建立起生物楔形结构。福柯用 *“种族主义(racism)"*这个似乎耳熟能详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点。 [15]
*种族(或者说种族主义)*在生命权力之计算中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种族思维比阶级思维(阶级是一种将历史定义为阶级间经济斗争的操作者)更作为自始至终地盘旋在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无处不在的阴影,尤其是当其目的是臆造外来民族之非人性以及对他们实施的统治类型时愈是如此。阿伦特在谈到这种无处不在的阴影以及种族的幽灵般的世界时,将它们的根源归结为 *“他者”*的破碎体验。她认为,种族政治最终是与死亡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16] 事实上,用福柯的话来说,种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旨在允许行使生命权力的技术,“即古老的杀人主权”。在生命权力经济中,种族主义的功能是调节死亡的分配,使国家的屠杀功能成为可能。他说,这是 “接受死刑的条件”。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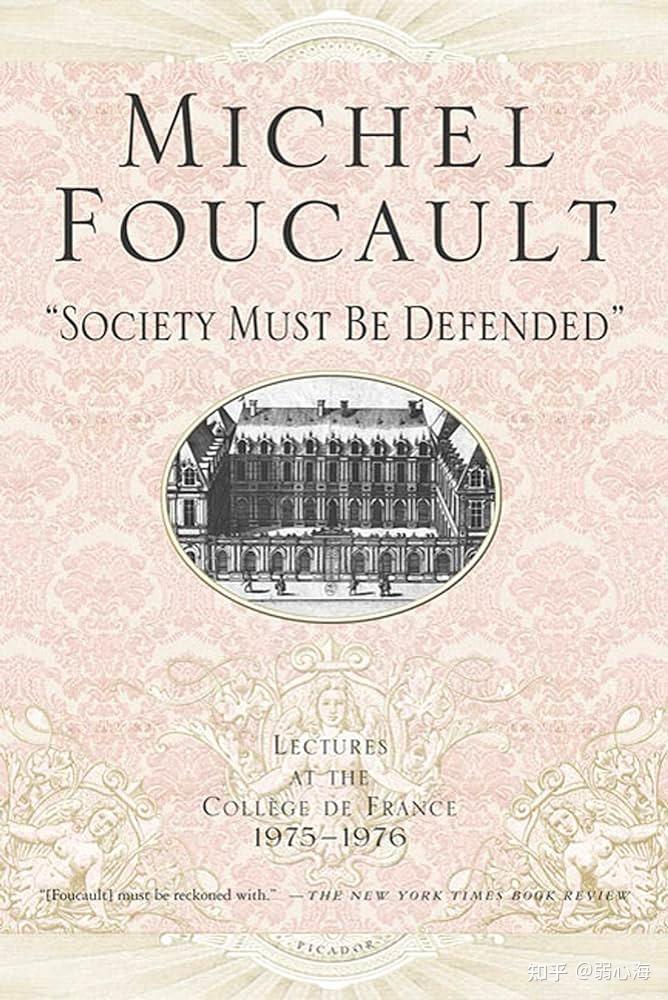
福柯明确指出,刀剑的主权与生命权力机制是所有现代国家运作的一部分; [18] 事实上,它们可被视为现代性国家权力之构成要素。他认为,纳粹国家是国家行使杀戮权的最完整的例子。他声称,这个国家将生命的管理、保护和培育与杀人之主权权利相提并论。他认为,通过对政治敌人这一主题的生物学推断,纳粹国家组织对其对手的战争,并同时让自己的公民卷入战争,为强大的杀戮权之巩固开辟了道路,并在 “最终解决方案”项目中达到顶峰。这样,它就成了集种族主义国家、嗜杀国家和自杀国家**特征于一身的权力形态之典型。
有人认为,纳粹国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战争与政治(以及种族主义、杀人和自杀)混为一谈,以至于使它们彼此无法区分。将他者之存在视为对我生命的企图,视为致命的威胁或绝对的危险,从生物物理上消除这种威胁或危险将增强我的生命潜能与安全感——我认为,这既是现代性早期的也是其晚期的主权所特有的诸多想象维度之一。对这种观念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大多数传统的现代性批判,无论是虚无主义及其将权力意志宣扬为存在之本质,还是被理解为人类成为客体的再化,抑或是万物从属于非个人逻辑以及可计算性、工具理性之统治。 [19] 事实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批判暗含着对将政治定义为卓越的战争关系的质疑。它们还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生命之计算必须通过他者之死亡,或者主权由杀戮以求生存的意志或能力构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许多分析家认为,一方面,纳粹灭绝的物质前提也存在于殖民帝国主义中,另一方面,存在于将人置于死地的技术机制之序列化中——这些机制是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根据*恩佐-特拉韦索(Enzo Traverso)*的观点,毒气室和焚尸炉是对死亡的非人化和工业化这一漫长过程的顶点,其最初特征之一是将工具理性与现代西方世界(工厂、官僚机构、监狱、军队)的生产和管理理性相结合。机械化之后,序列化的行刑变成了一种纯技术性、非个人化、无声而快速的程序。这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种族主义的成见和以阶级为基础的种族主义的兴盛,这种种族主义将工业世界的社会冲突转化为种族冲突,最终将工业世界的工人阶级和 “无国籍者 “与殖民世界的 “野蛮人 “相提并论。 [20]
实际上,现代性与恐怖之间的联系有多种来源。其中一些可以在古代政体之政治实践中找到。从这个角度看,公众对鲜血的热情与正义和复仇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至关重要。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描述道,对弑君者达米安的行刑持续了数小时,这让群众非常满意。 [21] 死刑犯在行刑前要在大街上进行长时间的游行,肢解尸体——这一仪式已成为大众暴力的标准特征之一——还要展览安插在长矛上的头颅。在法国,断头台之出现标志着处置国家敌人的手段进入了 ***“民主化”*的新阶段。事实上,这种曾经是贵族特权的行刑方式已扩展到所有公民。在斩首被认为没有绞刑那么有损尊严的背景下,谋杀技术的创新不仅旨在使杀人方式 “文明化”。它们还旨在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处理掉大量受害者。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出现了,在这种意识中,杀死国家的敌人是游戏之延伸。更亲密、更淫秽、更悠闲的残忍形式开始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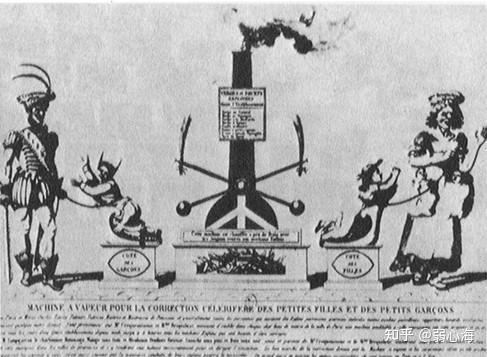
但是,理性与恐怖的混为一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22]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几乎被视为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国家与人民之间被认为是绝对透明的。作为一个政治范畴,“人民"逐渐从具体的现实变成了修辞上的形象。正如戴维-贝茨(David Bates)所指出的,恐怖理论家们认为可以区分主权的真实表达和敌人的行动。他们还认为,在政治领域,可以区分公民的 “错误"和反革命的 “罪行”。因此,恐怖成了标示政治体异常的一种方式,政治既被解读为理性之流动力量,也被解读为一种错误的尝试,试图创造一个空间,在那里,“错误"只会减少,真理会增强,敌人会被驱散。 [23]
最后,恐怖并不仅仅与乌托邦式的人类理性力量之不受束缚的信念有关。它显然还与各种关于主宰以及解放的叙事有关,其中大多数都以启蒙运动对真理与谬误、“真实"与象征的理解为基础。例如,马克思将劳动(维持人类生活所需的无休止的生产和消费循环)与工作(创造持久的人工制品,为世界万物添砖加瓦)混为一谈。劳动被视为人类历史性自我创造的载体。
历史之自我创造本身就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焦点是,什么样的道路才可能通向历史的真理:克服资本主义和商品形式,以及与它们各自相关的矛盾。马克思认为,随着康米主义的到来和交换关系之废除,事物将以其真实面目出现;“真实"将以其实际面目出现,主体与客体或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区别将被超越。 [24]但是,马克思把人类解放取决于商品生产的废除,从而模糊了人类创造的自由领域、自然决定的必然领域和历史中的偶然领域之间至关重要的划分。
废除商品生产的承诺和直接、无中介地接触 “真实"的梦想使得这些过程——所谓历史逻辑之实现和人类之创造——几乎必然是暴力的过程。正如斯蒂芬-卢瓦(Stephen Louw)所指出的那样,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信条让人们别无选择,只能 “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推行康米主义,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关系必须被强行去商品化”。 [25]从历史上看,这些尝试采取的形式包括劳动军事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的瓦解以及革命恐怖。 [26] 可以说,这些尝试都是为了消除人类多元性的基本条件。事实上,阶级分化之克服、国家之凋零、真实普遍意志的开花结果——所有这些都预先假定了一种观点,即人类之多元性是最终实现预定历史终极目标的主要障碍。换言之,马克思现代性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意图通过生死搏斗来证明其主权的主体。与黑格尔相似,这里的主宰和解放叙事显然与真理和死亡叙事相关联。恐怖和杀戮成为实现已知历史终极目标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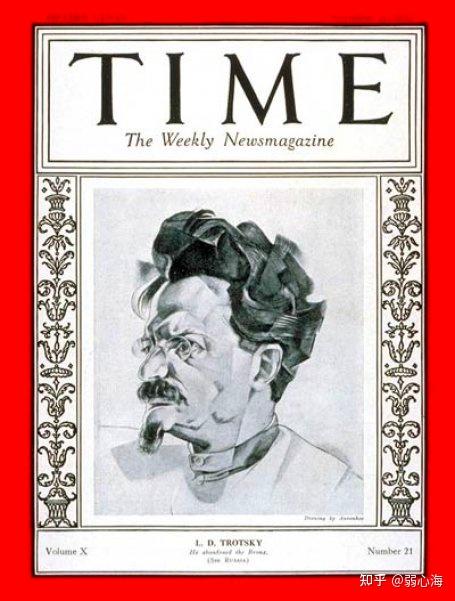
任何关于现代恐怖兴起的历史叙述都需要涉及奴隶制,奴隶制可被视为生命政治实验的最早实例之一。在许多方面,种植园制度的结构本身及其后果表达了例外状态的象征性和自相矛盾的形象。 [27] 在这里,这一形象之所以自相矛盾,有两个原因。首先,在种植园的背景下,奴隶之人性以阴影之完美形象出现。事实上,奴隶的处境是三重丧失的结果:失去 “家”、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和失去政治地位。这三重丧失与绝对统治、出身(natal)异化和社会死亡(被完全逐出人类)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法权结构,种植园是奴隶属于主人的空间。它之所以不是一个共同体,仅仅是因为从定义上讲,共同体意味着行使言论和思想的权力。正如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说:“种植园奴隶制所界定的极端交流模式,要求我们认识到权力在塑造交流行为时所产生的反话语的以及语言之外的影响。毕竟,在种植园里,除了叛乱和自杀、逃亡和无声哀悼的可能性之外,可能没有互惠,当然也没有语法上的统一性来调解交流的理性。在许多方面,种植园居民的生活都是非同时的(non-synchronously)"。 [28] 作为劳动工具,奴隶是有价的。作为一种财产,奴隶有其价值。奴隶之劳动是被需要的和使用的,因此,他虽然活着,但却是在受伤的状态下,在一个充满恐怖、残酷和亵渎的幽灵般的世界里。奴隶生活的暴力基调体现在监工的残忍和粗暴行为上,也体现在奴隶身体遭受痛苦的场面上。 [29] 在这里,暴力成了一种礼仪元素,就像鞭打或夺走奴隶的生命一样:是一种任性和纯粹的毁灭行为,旨在制造恐怖。 [30] 奴隶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生中之死。正如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所指出的那样,奴隶制在财产自由和人身自 由之间产生了矛盾。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随着支配生命的权力的不平等而建立起来。这种支配他人生命的权力以商业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人的人性被消解,以至于可以说奴隶之生命被主人占有。 [31] 由于奴隶的生命就像被他人占有的 “东西”,奴隶之存在就像影子一样完美。
尽管有这种恐怖的和象征性的封锁,奴隶仍然对时间、工作和自我保持着另一种视角。这是作为例外状态表现形式的种植园世界的第二个自相矛盾之处。奴隶被视为除了生产工具和工具之外不复存在的人,却能够将几乎任何物品、工具、语言或姿态引入表现(performance),然后将之风格化(stylize)。奴隶打破了被连根拔起的状态,也打破了自己只是其中一个片段的纯粹世界,他能够通过音乐和本应被他人占有的身体本身,展示人类纽带的无穷能力。 [32]

如果说在种植园制度下,生与死的关系、残酷的政治和亵渎的象征意义变得模糊不清,那么在殖民地和种族隔离制度下出现的则是一种奇特的恐怖形式,这就是我现在要谈到的。 [33] 这种恐怖形式最原始的特征是它将生命权力、例外状态和戒严状态结合在一起。种族再次成为这一组合的关键。 [34] 在大多数情况下,种族选择、禁止异族通婚、强制绝育,甚至灭绝被征服的民族,都是在殖民地世界找到的第一个试验场。大屠杀与官僚主义——西方理性之化身——在这里首次合成。 [35] 阿伦特提出了国家社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存在联系的论点。她认为,殖民征服揭示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潜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将以前只用于 “野蛮人"的方法扩展到欧洲的 “文明 “人民。
产生纳粹主义的技术起源于种植园或殖民地,或者——按照福柯的论述——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只是放大了西欧社会和政治形态中一系列已经存在的机制(身体征服、卫生法规、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关于遗传、退化和种族的医学法律理论),这些最终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有一个事实依然存在:在现代哲学思想中,在欧洲政治的想象和实践中,殖民地代表着一个地点(site),在那里,主权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法律之外行使权力(ab legibus solutus),在那里,“和平 “更有可能以 “无休止的战争"的面目出现。
事实上,这一观点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主权定义是一致的,即主权乃决定例外状态的权力。为了正确评估殖民地作为一种恐怖形式的效力,我们需要绕过欧洲想象本身,因为它涉及到战争之归化(domestication)与欧洲司法秩序之建立(Jus publicum Europaeum)这一关键问题。这一秩序的基础是两个关键原则。第一项原则假定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尤其适用于发动战争(夺取生命)的权利。发动战争的权利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杀戮或缔结和平被认为是任何国家的首要职能之一。与这一职能相辅相成的是,承认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其边界之外进行统治。但反过来说,国家也不能承认在其疆界内有凌驾于其之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家则致力于使杀戮方式 “文明化”,并为杀戮行为本身赋予合理的目标。

第二个原则涉及主权国家之领土化,即在新强加的全球秩序中确定其边界。 在这一秩序中,公共法迅速采取了区分的形式,一方面是全球可被殖民占有的地区,另一方面是欧洲(公共法将在欧洲发挥主导作用)。 [36]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区分对于评估殖民地作为恐怖结构的效力至关重要。 根据公共法,合法战争主要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乃 “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国家在战争计算中的核心地位源于国家是政治统一的典范、合理组织的原则、普世理念的体现以及道德标志。
同样,殖民地也类似于边疆。殖民地由 “野蛮人"居住,没有国家组织形式,也没有建立人类世界。它们的军队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们的战争也不是正规军之间的战争。它们并不意味着动员主权臣民(公民),彼此视对方为敌人。他们不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也不区分 “敌人"和 “罪犯”。 [37] 因此,与他们缔结和平是不可能的。总之,殖民地是战争与混乱、内部与外部政治人物并存或交替出现的地区。因此,殖民地是可以中止司法秩序的控制和保障的卓越场所——在这里,例外状态的暴力被认为是为 “文明"服务的。
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在绝对无法无天的状态下被统治,是因为征服者和当地人之间的种族纽带被否定了。在征服者眼中,野蛮人的生活只是动物生活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是一种无法想象或理解的异类。事实上,阿伦特认为,野蛮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人类,与其说是他们的肤色,不如说是他们的行为像自然的一部分,他们把自然当作无可争议的主人。因为大自然的一切威严依然是压倒一切的现实,与之相比,野蛮人就像是幻影、虚幻和幽灵。野蛮人可以说是 “自然"的人类,他们缺乏具体的人类特征,缺乏具体的人类现实,“因此,当欧洲人屠杀他们时,他们不知不觉地就犯下了谋杀罪”。 [38]

基于上述原因,在殖民地,主权的杀人权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在殖民地,主权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杀人。殖民战争不受法律和制度规则的约束。它不是一种法律编纂的活动。相反,殖民地之恐怖不断与殖民地产生的荒野幻想、死亡以及虚构交织在一起,产生一种真实的效果。 [39] 和平并不一定是殖民战争的自然结果。事实上,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别并不存在。殖民战争被视为征服者对绝对敌人的绝对敌意的表现。 [40] 欧洲法律想象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战争与敌意之所有表现形式都在殖民地重新出现。在这里,区分战争 ***“目的”***与 ***“手段”**的虚构不攻自破,同样,战争是一场受规则制约的较量,而不是没有风险或工具理性的纯粹屠杀的虚构也不攻自破。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重新诠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一书时,很好地抓住了战争难以解决的悖论之一:战争同时具有理性主义和明显的非人性。 [41]
晚期现代性的死亡权力与占有 #
也许有人会认为,上述观点与遥远的过去有关。在过去,帝国战争的目的确实是摧毁地方势力、安插军队,并对平民实施新的军事控制模式。一群地方辅助人员可以协助管理被征服并入帝国的领土。在帝国内部,给予战败者的地位意味着对他们的掠夺。在这些配置中,暴力构成了权利的原始形式,而例外则提供了主权的结构。帝国主义的每个阶段都涉及某些关键技术(炮舰、奎宁、蒸汽轮船线、海底电报电缆、殖民铁路)。 [42]
殖民占领本身包括夺取、划定和宣称对一个地理区域的控制——在当地书写一套新的社会和空间关系。书写新的空间关系(领土化)最终等同于制造边界和等级制度、区域和飞地;颠覆现有的财产安排;对人进行有区别的分类;开采资源;最后是制造大量的文化想象。这些想象赋予了为不同类别的人确立不同权利的意义,这些权利具有不同的目标,但存在于同一空间——简而言之,就是行使主权。因此,空间是主权及其所包含的暴力的原材料。主权意味着占领,占领意味着将殖民者置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第三区域。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如此。在这里,*乡镇(township)*是一种结构形式,而家园则成为保留地(农村基地),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调节移民劳工的流动,控制非洲的城市化进程。 [43] 正如贝琳达-博佐利(Belinda Bozzoli)所言,乡镇尤其是 “在种族和阶级基础上经历严重压迫和贫困"的地方。 [44]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乡镇是一种为控制目的而科学规划的特殊空间机构。 [45] 自治地和乡镇的运作要求严格限制黑人为白人地区的市场进行生产,终止黑人的土地所有权(保留区除外),将黑人在白人农场的居住非法化(受雇于白人的仆人除外),控制城市人口流入,以及后来对非洲人之公民权的剥夺。 [46]
弗朗茨-法农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殖民占领的空间化。他认为,首先,殖民占领需要将空间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它涉及以兵营和警察局为缩影的边界和内部疆界的设置;它以纯粹的武力、直接的存在以及频繁而直接的行动为语言规范;它以互惠排他性原则为前提。 [47] 但更重要的是,这就是死亡权力之运作方式: “属于殖民地人民的城镇……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到处都是声名狼藉的人。他们在那里出生,在哪里或如何出生并不重要;他们在那里死亡,在哪里或如何死亡也不重要。那里是一个不宽敞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偎着生活。故乡是一座饥饿的城市,没有面包,没有肉,没有鞋,没有煤,没有光。故乡是一个蹲着的村庄,一个跪伏的城市”。 [48]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意味着界定谁重要、谁不重要,谁可支配、谁不可支配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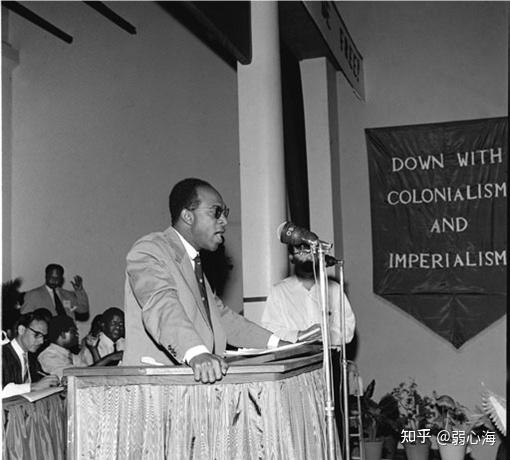
晚期现代殖民占领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早期现代占领,尤其是在将纪律/规训、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necropolitical)*相结合方面。当代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占领是最成功的死亡权力形式。在这里,殖民国家对主权和合法性的基本诉求来自于其自身特定的历史与身份叙事之权威性。这种叙事本身的基础是国家拥有神圣的生存权,这种叙事与另一种叙事争夺同一神圣空间。由于这两种叙事互不相容,两种人群又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在纯粹的身份基础上划分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和主权都有一个神圣的基础:*民族意识(peoplehood)本身就是通过对一个神灵的崇拜而形成的,而民族身份则被想象为一种反对他者、反对其他神灵的身份。 [49] 历史、地理、地图学和考古学被认为是这些主张之后盾,从而将身份与地形(topography)*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殖民暴力和占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真理与排他性的神圣恐怖所支撑的(大规模驱逐、将 “无国籍 “的人安置在难民营、建立新殖民地)。在神圣的恐怖之下,是不断出土的遗骨;是对被撕裂的躯体的永久记忆,这些躯体被凿成千百块,永远不会是同一个人;是对 ***“原罪(original crime)”***的限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自己之 “原罪”的,对一种无法言说的死亡的,代表之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representing for oneself an “original crime,” an unspeakable death):这就是大屠杀之恐怖。 [50]
回到法农对殖民占领的空间解读,现代晚期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占领呈现出三大特点,涉及我称之为 *“死亡权力(necropower)"*之特定恐怖结构的运作。首先是领土分裂的动态——定居点之封锁和扩张。这一进程有双重目标:将所有行动都渲染得不可能,并按照种族隔离国家的模式实施各种形式的隔离。因此,被占领土被分割成错综复杂的内部边界网和各种孤立的单元。埃亚尔-魏兹曼(Eyal Weizman)认为,分散和分割脱离了领土之平面划分,而采用了在领土内建立三维边界的原则,从而明确地重新定义了主权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51]

魏茨曼认为,这些行动构成了 “纵向政治(the politics of verticality)”。由此产生的主权形式可以定性为 “垂直主权(vertical sovereignty)"。在垂直主权的体制下,殖民占领是通过立交桥与地下通道的计划来运作的,是领空与地面的分离。地面本身分为地壳和底土(subsoil)。殖民占领还受制于地形及其地貌变化(山顶和山谷、山脉和水体)的性质。因此,高地具有山谷所不具备的战略优势(更好的视野和自我保护能力,可将目光投向多个方向的全景式防御工事)。正如魏茨曼所说,“定居点可以被视作监视以及行使权力的城市光学装置"。在晚期现代殖民占领的条件下,监视既面向内部也面向外部,眼睛充当武器,反之亦然。魏兹曼称,“西岸特殊地形之组织结构创造了多重分隔、临时边界,它们通过监视和控制相互关联”,而不是通过一条边界线将两个国家最终划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占领不仅等同于控制、监视和隔离,而且也是孤立的同义词。这是一种分裂性、*碎片性(splintering)*占领,与晚期现代性所特有的分裂性城市主义(郊区飞地或封闭社区)相一致。 [52]
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殖民占领之分裂、碎片形式以快速***绕行/旁路(bypass)***道路、桥梁和隧道网络为特征,它们相互交织,试图维持法农式的 “交互排他性原则(principle of reciprocal exclusivity)”。魏兹曼认为,“旁路道路试图将以色列的交通网络与巴勒斯坦的交通网络分开,最好是不允许它们交叉。因此,旁路道路强调的是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种不同地理环境的重叠。在交通网交叉的地方,就会形成临时隔离带。最常见的情况是,挖出尘土飞扬的小路,让巴勒斯坦人从快速、宽阔的高速公路下穿过,以色列货车和军用车辆在这些高速公路上穿梭于定居点之间”。 [53]

在这种纵向主权与殖民占领分裂之条件下,社区沿着 Y 轴被分割开来。暴力场所也随之增多。战场不仅仅位于大地表面。地下和空中也变成了冲突地区。地面和天空之间不存在连续性。就连领空的边界也被划分为下层和上层。到处都在重申顶层(谁在顶层)之象征意义。因此,对天空的占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大部分警务工作都是从空中进行的。为此,各种其他技术也被调动起来:无人驾驶飞行器上的传感器、空中侦察喷气机、预警鹰眼飞机、攻击直升机、地球观测卫星、“全息图 “技术。杀戮变得有的放矢。
这种精确性与中世纪攻城战的战术相结合,适用于网络化扩张的城市难民营。对敌人的社会和城市基础设施网络进行精心策划的系统性破坏,是对陆地、水域和空域资源侵占、挪用的补足。这些使敌人丧失能力的技术中至关重要的是推土机:拆毁房屋和城市、连根拔起橄榄树、用子弹击穿水箱、轰炸和干扰电子通讯、挖掘道路、毁坏变压器、拆毁机场跑道、瘫痪电视和无线电发射机、砸毁计算机、洗劫原巴勒斯坦国的文化和政治官僚象征以及掠夺医疗设备——换句话说,就是基础设施战(infrastructural warfare)。 [5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用于空中警戒和杀戮,而装甲推土机(卡特彼勒 D-9)则在地面上用作战争和恐吓武器。与早期现代殖民占领相比,这两种武器都确立了晚期现代恐怖高科技工具的优势。 [55]

巴勒斯坦的情况说明,晚期现代殖民占领是多种权力的结合:规训权力、生命政治权力和死亡政治权力。三者的结合赋予了殖民国家对被占领土居民的绝对统治权。围困(siege)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军事体制。它允许一种不区分内外敌人的杀戮方式。整个人口都是主权之目标。被围困的村镇被封锁,与世隔绝。日常生活被军事化。地方军事指挥官可自行决定何时向谁开枪。在领地单元之间行动需要正式许可。当地的民间机构被系统性地摧毁。被围困的居民被剥夺了收入来源。除了直接处决之外,还有隐形杀戮。
战争机器与他律 #
在研究了现代晚期殖民占领条件下死亡权力的运作之后,我现在想谈谈当代战争。当代战争属于一个新的时代,很难通过早期的 ***“契约暴力(contractual violence)”**理论或 “正义"与 “非正义 “战争的类型学,甚至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工具论来理解。 [56]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战争不以征服、获取和接管领土为目标。理想情况下,它们是肇事逃逸(hit-and-run)*的事务。
高技术和低技术战争手段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从未像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役那样明显。在每一次战争中,“压倒性或决定性武力 “理论都得到了充分实施,这要归功于军事技术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强了破坏能力。 [57] 与高度、弹药、能见度和情报有关的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海湾战争中,智能炸弹和贫铀弹、高科技对峙武器、电子传感器、激光制导导弹、集束炸弹和窒息弹、隐形能力、无人驾驶飞行器以及网络情报的综合使用迅速削弱了敌人的能力。

在科索沃,”降格(degrading)“塞尔维亚能力的形式是一场基础设施战争,目标是摧毁桥梁、铁路、公路、通信网络、储油库、供热厂、发电站和水处理设施。可以推测,执行这样的军事战略,尤其是在实施制裁的同时,会导致敌人的生命支持系统瘫痪。对平民生活造成的持久损害尤其能说明问题。例如,在科索沃战役期间,位于贝尔格莱德郊区的潘切沃石化联合企业被摧毁,“附近地区被乙烯基氯化物、氨、汞、石脑油和二恶英毒化,孕妇被指示去堕胎,所有当地妇女被建议两年内不要怀孕”。 [58]
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旨在迫使敌人屈服,而不考虑军事行动的直接后果、副作用或 “附带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战争更像是游牧民族(nomad)的战争策略,而不是定居民族的战争策略,或是现代性的 “征服-吞并 “领土战争。用鲍曼的话说,“他们对定居人口的优势在于他们自身的移动速度;他们自身能够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不知何处降临,又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再次消失,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不需要携带那种限制定居人口的移动性和机动潜能的物品”。 [59]
这是一个全球流动的新时代。全球流动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不再垄断军事行动和行使杀戮权,“正规军"也不再是履行这些职能的唯一手段。在特定的政治空间中,对根本或最终权威的要求并不容易实现。取而代之的是重叠和残缺的统治权的拼凑,这些权利不可避免地叠加和纠缠在一起,不同的事实司法实例在地理上相互交织,多元效忠(plural allegiances)、不对称宗主国和飞地比比皆是。 [60]在这种领土权利和主张的同名异义的(heteronymous)组织中,坚持明确划分 “内部 “和 “外部 “政治领域的界限是毫无意义的。
以非洲为例,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非洲的国家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非洲国家再也不能声称自己垄断了境内的暴力或胁迫/强制手段。它们也不能声称垄断了领土边界。***胁迫/强制(Coercion)***本身已成为一种市场商品。军事力量在市场上买卖,供应者和购买者的身份几乎毫无意义。城市民兵、私人军队、地区领主军队、私人安保公司和国家军队都声称有权使用暴力或杀人。邻国或反叛运动向穷国租借军队。非国家暴力部署者提供两种关键的强制性资源:劳动力和矿产。越来越多的军队由公民士兵、儿童兵、雇佣兵和私掠者组成。 [61]
因此,我们可以效仿德勒兹和瓜塔里,将与军队同时出现的东西称为战争机器(war machines)。 [62] 战争机器是由武装人员组成的,他们根据所要执行的任务和所涉及的情况,彼此分裂或合并。战争机器是多形态的分散组织,其特点是具有变形能力。它们与空间的关系是流动的。它们有时与国家形式有着复杂的联系(从自治到合并、一体化)。国家可以自行将自身转变为战争机器。此外,它还可以将现有的战争机器据为己有,或帮助创建战争机器。战争机器之运作借鉴了正规军的经验,同时融入了适应分段和解域化原则的新元素。反过来,正规军也可以随时借鉴战争机器的某些特点。

战争机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它具有政治组织和商业公司的特征。它通过俘虏和掠夺进行运作,甚至可以铸造自己的货币。战争机器与跨国网络建立直接联系,为开采和出口其控制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燃料。战争机器是 20 世纪最后 25 年在非洲出现的,这与后殖民国家建立政治权威和秩序的经济基础的能力受到侵蚀有直接关系。这种能力包括在明确界定的领土内增加收入、控制和管理自然资源之获取。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维持这种能力的能力开始受蛀蚀而降格、削弱,货币不稳定与空间分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联系。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一些国家经历恶性通货膨胀(包括突然更换货币等惊人绝技),货币贬值的残酷经历变得更加普遍。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货币流通至少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和社会。
首先,我们看到流动资金普遍枯竭,并逐渐向特定渠道集中,而获得流动资金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因此,拥有物质手段通过债务控制受扶养人的个体数量骤然减少。从历史上看,通过债务机制俘获和控制、稳住受扶养人是人口生产和政治纽带构成的核心环节。 [63] 这种纽带对于确定人之价值和衡量人之效用至关重要。当他们的价值和效用得不到证明时,他们就会被当作奴隶、棋子或客户处理掉。
其次,在开采特定资源的地区,受控制的资金流入和固定的资金流动使得飞地经济之形成得以可能,从而改变了人与物之间的旧有计算方式。与开采宝贵资源有关的活动集中在这些飞地周遭,反过来又将飞地变成了战争和死亡的特权空间。战争本身也因开采产品的销售量增加而加剧。 [64] 因此,战争、战争机器和资源开采之间出现了新的联系。 [65] 战争机器参与构成了高度跨国的地方或区域经济。在大多数地方,正规政治体制在暴力压力下的崩溃往往会导致***民兵/武装经济(militia economies)***之形成。战争机器(这里指民兵或反叛运动)迅速成为高度组织化的掠夺机制,对其占领的领土和人口征税,并利用一系列跨国网络和侨民提供物质和资金支持。

与新的资源开采地理学相关的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府管理形式,其内容是管理诸众(multitudes)。战争机器在开采和掠夺自然资源的同时,还野蛮地*试图将*人之整体范畴(whole categories of people)固定下来,或者,自相矛盾的是,将他们解放出来,迫使他们分散到不再受领土国家边界限制的广阔地区。作为一种政治类别,人口被细分为反叛者、儿童兵、受害者或难民,或因肢体伤残而丧失行动能力的平民,或按照古代献祭的模式被简单屠杀的平民,而在经历了可怕的逃亡之后,“幸存者 “被限制在营地和例外地区。 [66]
这种治理形式不同于殖民统治。 [67] 行使警察权威和纪律的技术,在**服从(obedience)和模拟(simulation)之间做出选择,是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强权的特点,正逐渐被另一种更悲惨、更极端的选择所取代。在生死抉择的背景下,破坏技术变得更加触觉化(tactile)、解剖化(anatomical)和感官化(sensorial)。 [68] 如果说权力仍然依赖于对身体的严密控制(或将身体集中到集中营),那么新的毁灭技术则不那么关注将身体置于惩戒机构中,而是关注在时机成熟时,将身体置于 “大屠杀"所再现的最大经济秩序中。反过来,不安全感之普遍化又加深了社会对持有武器者和不持有武器者的区分(武器分配法则)。越来越多的战争不再是两个主权国家之军队之间的战争,而是在国家面具下行动的武装团体与并无国家但却控制着截然不同领土的武装团体之间的战争,双方的主要目标都是手无寸铁或组织成民兵的平民。在武装异己分子尚未完全夺取国家政权的情况下,他们挑起领土分裂,成功控制了整个地区,并以藩属国的模式对其进行管理,尤其是在蕴藏矿藏的地区。 [69]
屠杀的方式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大屠杀的情况下,了无生机的尸体很快就会沦为草草的骷髅。他们的*形态(morphology)*从此被刻录在别无二致的普遍性登记簿上:未埋葬的痛苦的简单遗物;空洞、无意义的肉体;陷入残酷昏厥的奇特沉积物。在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中,一些骸骨在没有被挖掘出来时,一直保持着可见的状态——令人震惊的是,一方面,骸骨之石化与它们奇异的冷漠,另一方面,它们顽固地想要表达某种意思,象征某种东西,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在这些麻木安静的碎骨中,似乎并不存在 “安乐死”(ataraxia):只有对已经发生的死亡的虚幻拒绝。在其他情况下,截肢取代了直接死亡,断肢为以骨头为目标的切口、消蚀和割除技术之应用铺平了道路。这种造物主外科手术留下的痕迹会持续很长时间,表现为人的形状,当然,这些形状还活着,但其身体之完整性已被裂片、碎块、褶皱所取代,即使是巨大的伤口也不容易愈合。它们的作用就是在受害者和周围人的眼前永远呈现出这种割裂的病态景象。
行为的与金属的 #
让我们回到巴勒斯坦的例子,在那里,我们看到两种显然不可调和的逻辑之间发生了对抗:***殉难(martyrdom)之逻辑与生存(survival)***之逻辑。在研究这些逻辑时,我想思考死亡与恐怖,以及,恐怖与自由这两个问题。
在这两种逻辑的对峙中,恐怖与死亡并不站在彼此的对立面。恐怖和死亡是这两种逻辑的核心。正如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提醒我们的那样,幸存者是站在死亡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次死亡,置身于倒下的人之中,却依然活着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幸存者是在面对一大群敌人时,不仅能活着逃脱,而且还能杀死攻击者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杀戮是最低级的生存方式。卡内蒂指出,在生存逻辑中,“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更为彻底的是,在生存的逻辑中,目睹死亡时的恐怖感会转化为对死者乃他人的满足感。正是 “他人"之死亡,“他人"作为尸体的存在,让幸存者感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而每杀死一个敌人,都会让幸存者更有安全感。 [70]
殉难之逻辑遵循迥异的路线。“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之形象就是这种逻辑的缩影: 用导弹直升机或坦克杀人与用自己的身体杀人有什么本质区别?用以制造死亡的武器之间的区别是否会妨碍在杀人方式和死亡方式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交换制度?

自杀炸弹手不穿饰普通士兵的制服,也不振臂挥舞武器。殉难之对象乃猎物;敌人是陷阱中的猎物。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埋伏地点:公共汽车站、咖啡馆、迪斯科舞厅、集市、检查站、公路——总之,日常生活的各个空间。
除了埋伏地点之外,还有身体陷阱。殉难者之身体会变成一幅面具,掩盖即将引爆的武器。坦克或导弹清晰可见,而以身体形状携带的武器却是隐形的。武器就这样被隐藏起来,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它是身体如此紧密的一部分,以至于在引爆时,它摧毁了携带者自己的身体,即使没有把其他人的身体炸成碎片,也会把他们的身体一起炸成碎片。身体并不只是隐藏着武器。身体变成了武器,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武器,而是真正***弹道学(ballistic)***意义上的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死亡与他者的死亡同时发生。杀人和自杀在同一行为中完成。反抗与自我毁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词。因此,实施死亡就是将他人与自己还原、贬低为惰性肉体之碎片,散落各处,在下葬前再艰难地拼凑、缝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是身体对身体的战争(guerre au corps-à-corps )。要杀人,就必须尽可能靠近敌人的身体。要引爆炸弹,就必须通过趋近与隐匿来解决距离问题。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泼撒鲜血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死亡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死亡,而总是与他人之死亡同时发生? [71] 在我的生存代价是以我杀死他人的能力以及为杀死他人而就绪、预备到何等意愿程度来计算的情况下,它与坦克或导弹造成的死亡有何不同?在 “殉难"的逻辑中,死亡之意志与将敌人一并击倒的意志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要关上所有人的生命可能性之门。这种逻辑似乎与另一种逻辑背道而驰,后者是希望将死亡强加于他人,同时保全自己的生命。卡内蒂将这种生存时刻描述为权力时刻(a moment of power)。在这种情况下,胜利正是源于当他人(这里指敌人)不再存在时,自己仍有可能存在。这就是经典所理解的英雄主义逻辑:处决他人的同时与自己的死亡保持距离。
殉难逻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杀戮符号学。它并不一定建立在形式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上。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身体在这里成为殉道者之制服与符号(uniform)。但是,身体本身并不仅仅是用以抵御危险与死亡的对象。身体本身既没有力量,也没有价值。相反,它的力量与价值来自于基于永恒渴望的抽象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殉道者在建立了主体战胜自身死亡的至高无上的时刻之后,可以被视作在未来之征兆、符号(uniform)下劳作。换言之,在死亡中,未来被坍缩为当下。
在对***永恒(eternity)***的渴望中,被围困的身体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它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的东西,一种可塑的物质。其次,它的死亡方式——自杀——赋予了其最终的意义。身体之物质,或者说身体所是的物质,被赋予了一些属性,这些属性不是从它作为事物的特性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它之外的先验的(transcendental)法则(nomos)中推导出来的。被围困的身体变成了一块金属,其功能是通过牺牲以带来永恒的生命。身体复制了自身,重复了自身,并在死亡中从字面上和隐喻上摆脱了被围困、被戒严和被占领的状态。
最后,让我探讨一下恐怖、自由与牺牲(sacrifice)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人的 “向死而生"是一切真正的人类自由之决定性条件。 [72] 换言之,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是因为他能够自由地死去。海德格尔赋予 “向死而生(being-toward-death)”以存在论的地位,并将其视为自由之事件,而巴塔耶则认为,“牺牲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揭示(sacrifice in reality reveals nothing)”。它不仅仅是消极性的绝对体现。它还是一出喜剧。在巴塔耶看来,死亡揭示了人类主体之动物性一面,他将其称为主体之 “自然存在(natural being)"。他还说:“人最终要揭示自己,就必须死亡,但他必须在活着的时候揭示自己,目睹着自己不复存在”。换言之,人类主体在死亡的那一刻必须完全活着,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带着实际死亡的感觉与印象生活。死亡本身必须在泯灭意识存在的同时成为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通过牺牲之潜规则而发生的事情(至少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模糊的方式发生的事情)。在牺牲、献身的过程中,被牺牲者在死亡的那一刻将自己与动物相提并论。这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自己的意志,与牺牲之武器,与祭品,合二为一。但这就是游戏(play)!” 在巴塔耶看来,游戏或多或少是人类主体 “自愿欺骗自己 “的手段。 [73]

游戏和诡计(trickery)的概念与人体炸弹有什么关系?就自杀炸弹手而言,牺牲无疑是壮观地将自己置于死地,成为自己的牺牲品(自我牺牲)。自我牺牲者通过直面死亡,掌握了对死亡的控制权。这种力量可能来自这样一种信念,即摧毁自己的身体并不会影响存在之连续性。这种想法认为存在于我们之外。在这里,自我牺牲包括解除双重禁令:自焚(自杀)禁令与殉葬禁令。然而,与原始祭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动物作为替代牺牲品。在这里,死亡具有***僭越(transgression)***的性质。但与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同的是,它没有赎罪的意义。它与黑格尔式的出类拔萃、***声誉(prestige)或承认(recognition)***之范式无关。事实上,一个死人无法识别、承认杀害他的凶手,而凶手也已经死了。这是否意味着这里的死亡是纯粹的毁灭与虚无、过度与丑闻?
无论是从奴隶制的角度还是从殖民占领的角度来看,死亡与自由都不可逆转地交织在一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恐怖乃奴隶制和晚期现代殖民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两种制度也都是不自由的具体实例和经历。在晚期现代占领下生活,就是在经历一种永久的 “痛苦(being in pain)": 坚固的建筑、军事哨所和路障随处可见;建筑物勾起了人们对侮辱、审讯与殴打的苦楚回忆;宵禁将成千上万的人囚禁在狭窄的居所中,每晚从黄昏到黎明;士兵在灯光熹黯的街道上巡逻,被自己的影子吓一跳;儿童被橡皮子弹射瞎了双眼;父母在家人面前遭受蒙羞与殴打; 士兵们在栅栏上撒尿,为了找乐子而向屋顶的水箱发射子弹,扯着嗓门吆喝攻击性的口号,敲击锈迹斑斑的铁皮门吓唬孩童,没收证件,或在居民区中央倾泻垃圾;边防军一脚踢翻菜摊或任性地关闭边境;骨折;枪击以及死亡——这是一种疯狂(madness)。 [74]

在这种情况下,生命之规训与艰难困苦(死亡的考验)之必要性都带有***过度(excess)的特征。连接恐怖、死亡与自由的是一种狂喜(ecstatic)的时间性与政治之概念。在这里,未来可以被准确地、原貌地预期,但不是在当下。当下本身不过是视觉、愿景(vision)***之一瞬间——对尚未到来的自由的愿景。当下的死亡乃救赎之中介。它远非与限制、边界或障碍的相遇,而是被体验为 “(从)恐怖与束缚中的释放”。 [75] 正如吉尔罗伊(Gilroy)所指出的,这种对死亡而非继续奴役的偏爱,是对自由本身(或缺乏自由)的本质的评论。如果说这种匮乏乃奴隶或殖民者存在之本质,那么这种匮乏也恰恰是他考虑自己死亡的方式。吉尔罗伊在谈到被捕奴者逼入绝境的奴隶的个人或集体式自杀行为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可以表现为一种能动性。因为死亡恰恰是我所拥有的权力。但它也是自由和否定的运作空间。
在本章中,我论证了将生命置于死亡权力之下的当代形式*(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正在深刻地重构抵抗、牺牲以及恐怖之间的关系。我已经证明,生命权力的概念不足以解释当代生命屈从于死亡权力的形式。此外,我还提出了 *“死亡政治学 (necropolitics)"*或 “死亡权力(necropower)"的概念,以解释在我们的当代世界中,为了最大限度地毁灭人类和创造死亡世界而部署武器的各种方式,即新的和独特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这种社会存在形式中,大量人口的生活条件赋予了他们活死人的地位。我还概述了一些被压抑的残酷地形(特别是种植园和殖民地),并指出当今的死亡权力形式模糊了抵抗与自杀、牺牲与救赎、殉难与自由之间的界限。
参考 #
- ^本文仅作翻译,不代表译者立场.
- ^The essay departs from the traditional accounts of sovereignty to be found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accounts locate sovereignt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state, state-empowered institutions, or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 See, for example,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special issue of Political Studies 47 (1999). My own approach builds on Foucault’s critique of the notion of sovereignty and its relation to war and biopower in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 ed.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o,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65–86, 87–114, 141–66, 239–64. See also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67.
- ^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 239–64.
- ^On the state of exception, see Carl Schmitt, Dictatorship , trans. Michael Hoelzt and Graham War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4), 181–94, 200–201, 205–7, 218–19; Carl Schmitt, Theory of the Partisa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 trans. A. C. Goodson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vest, 1966), 444.
-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 trans.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39–40.
- ^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 trans. Kathleen Blamey (Oxford: Blackwell, 1987); and Figures of The Thinkable , trans. Helen Arno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See, in particular,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specially chap. 2.
- ^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 ed. and trans. Terry Pinkard and Micheal Bau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See also the critique by Alexandre Kojève, Instr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7), especially appendix II, “The Idea of Death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Georges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XII (Paris: Gallimard, 1988), especially “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326–48 (In English: “Hegel, Death and Sacrifice,” trans. Jonathan Strauss, “On Bataille,” special issue of Yale French Studies , no. 78 [1990]: 9–28), and “Hegel, l’homme et l’histoire,” 349–69.
- ^See Jean Baudrillard, “Death in Bataille,” in Bataille: A Critical Reader , ed. 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 (Oxford: Blackwell, 1998), especially 139–41.
- ^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 trans. A. Stoek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94–95.
- ^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 eds., The Bataille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7), 318–19. See also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 vol. 1, Consumption ,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1988), and Erotism: Death and Sensuality , trans. Mary Dalwood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1986).
-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 vol. 2,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and Sovereignty ,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2).
- ^On the state of siege, see Schmitt, Dictatorship , chap. 6.
- ^See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 61–62, 65–80.
- ^“Race is, politically speaking, not the beginning of humanity but its end … not the natural birth of man but his unnatural death.”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157.
- ^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 256, 241.
-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 240–45.
- ^See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 trans. Frederick G. Lawr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especially chaps. 3, 5, 6.
- ^Enzo Traverso, La violence nazie: Une généalogie européenne (Paris: La Fabrique Editions, 2002).
- ^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1977).
- ^See Robert Wokler, “Contextualizing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Terror,” Political Theory 26 (1998): 33–55.
- ^David W. Bates, Enlightenment Aberrations: Error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 6.
-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4), 3:817. See also Capital , trans.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86), 1:172.
- ^ Stephen Louw, “In the Shadow of the Pharaohs: The Militarization of Labour Debate and Classical Marxist Theory,” Economy and Society 29 (2000): 240.
- ^ On labor militar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communism, see Nikolai Bukhari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 trans. Oliver Fiel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Leon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Reply to Karl Kautsk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On the collapse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see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oscow: Progress, 1972); Vladimir Il’ich Lenin,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 vol. 2 (Moscow: Progress, 1977). For a critique of “revolutionary terror,” see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An Essay on the Communist Problem , trans. John O’Neill (Boston: Beacon, 1969). For a more recent example of “revolutionary terror,” see Steve J. Stern, ed., Shining and Other Paths: War and Society in Peru, 1980–1995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See Saidiya V. Hartman, Scenes of Subjection: Terror, Slavery, and Self-Ma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nuel Moreno Fraginals, The Sugarmill: The Socioeconomic Complex of Sugar in Cuba, 1760–186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Gilroy, Black Atlantic , 57.
- ^See Frederick Douglass,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 ed. Houston A. Baker (New York: Penguin, 1986).
- ^The term “manners” is used here to denote the links between social grace and social control . According to Norbert Elias, manners embody what is “considered socially acceptable behavior,” the “precepts on conduct,” and the framework for “conviviality.” The History of Manners , vol. 1, The Civilizing Process ,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1978), chap. 2. Douglass, Narrative of the Life , 51. On the random killing of slaves, see 67–68: “The louder she screamed, the harder he whipped; and where the blood ran faster, there he whipped longest,” says Douglass in his narration of the whipping of his aunt by Mr. Plummer. “He would whip her to make her scream, and whip her to make her hush; and not until overcome by fatigue, would he cease to swing the blood-clotted cowskin.… It was a most terrible spectacle.”
- ^ Susan Buck-Morss, “Hegel and Haiti,” Critical Inquiry 26 (2000): 821–66.
- ^Roger D. Abrahams, Singing the Master: The Emergence of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Plantation South (New York: Pantheon, 1992).
- ^ In what follows I am mindful of the fact that colonial forms of sovereignty were always fragmented. They were complex, “less concerned with legitimizing their own presence and more excessively violent than their European forms.” As important, “European states never aimed at governing the colonial territories with the same uniformity and intensity as was applied to their own populations.” T. B. Hansen and Finn Stepputat, “Sovereign Bodies: Citizens, Migrants and States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2.
- ^In The Racial State (Malden, MA: Blackwell, 2002), David Theo Goldberg argues that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 there are at least two historically competing traditions of racial rationalization: naturism (based on an inferiority claim) and historicism (based on the claim of the historical “immaturity”—and therefore “educability”—of the natives). In a private communication (August 23, 2002), he argues that these two traditions played out differently when it came to issues of sovereignty, states of exception, and forms of necropower. In his view, necropower can take multiple forms: the terror of actual death or a more “benevolent” form—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destruction of a culture in order to “save the people” from themselves.
-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185–221.
- ^Etienne Balibar, “Prolegomena to Sovereignty,” in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 trans. James Swen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3–54.
- ^Eugene Victor Walter, Terror and Resistance: A Study of Political Violence with Case Studies of Some Primitive African Comm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192.
- ^For a powerful rendition of this process, see Michael Taussig,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On the notion of “enemy,” see “L’ennemi,” special issue of Raisons politiques , no. 5 (2002).
-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
- ^See Daniel R.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On the township, see G. G. Maasdorp and A. S. B. Humphreys, eds., From Shantytown to Township: An Economic Study of African Poverty and Rehousing in a South African City (Cape Town: Juta, 1975).
- ^Belinda Bozzoli, “Why Were the 1980s ‘Millenarian’? Style, Repertoire, Space and Authority in South Africa’s Black Citi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3 (2000): 79.
- ^Bozzoli, “Why Were the 1980s ‘Millenarian’?”
- ^See Herman Giliomee, ed., Up Against the Fences: Poverty, Passes and Privileges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David Philip, 1985); Francis Wilson, Migrant Labour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Christian Institute of Southern Africa, 1972).
-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 trans. C.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 39.
- ^Fanon, Wretched of the Earth , 37–39.
- ^See Regina M. Schwartz, The Curse of Cain: The Violent Legacy of Monothe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See Lydia Flem, L’Art et la mémoire des camps: Représenter exterminer , ed. Jean-Luc Nancy (Paris: Seuil, 2001).
- ^ See Eyal Weizman, “The Politics of Verticality,” openDemocracy , April 25, 2002, https:// www .opendemocracy .net /ecology -politicsverticality /article _801 .jsp .
- ^ See Stephen Graham and Simon Marvin,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y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 ^Weizman, “Politics of Verticality.”
- ^ See Stephen Graham, “‘Clean Territory’: Urbicide in the West Bank,” openDemocracy , August 7, 2002, https:// www .opendemocracy .net /conflict -politicsverticality /article _241 .jsp .
- ^Compare with the panoply of new bombs the United States deployed during the Gulf War and the war in Kosovo, most aimed at raining down graphite crystals to disable comprehensively electrical power and distribution stations. Michael Ignatieff, Virtual War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 ^See 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 ^Benjamin Ederington and Michael J. Mazarr, eds., Turning Point: The Gulf War and U. S. Military Strategy (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 ^Thomas W. Smith, “The New Law of War: Legitimizing Hi-Tech and Infrastructural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6 (2002): 367. On Iraq, see G. L. Simons, The Scourging of Iraq: Sanctions, Law and Natural Justice ,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see also A. Shehabaldin and W. M. Laughlin Jr. ,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Iraq: Human and Economic Co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3, no. 4 (2000): 1–18.
- ^Zygmunt Bauman, “Wars of the Globalization Er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4, no. 1 (2001): 15. “Remote as they are from their ‘targets,’ scurrying over those they hit too fast to witness the devastation they cause and the blood they spill, the pilots-turned-computer-operators hardly ever have a chance of looking their victims in the face and to survey the human misery they have sowed,” adds Bauman. “Military professionals of our time see no corpses and no wounds. They may sleep well; no pangs of conscience will keep them awake” (27). See also Zygmunt Bauman, “Penser la guerre aujourd’hui,” Cahiers de la Villa Gillet , no. 16 (2002): 75–152.
- ^Achille Mbemb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Boundaries, Territoriality, and Sovereignty in Africa,” Public Culture 12 (2000): 259–84.
- ^In international law, “privateers” are defined as “vessels belonging to private owners, and sailing under a commission of war empowering the person to whom it is granted to carry on all forms of hostility which are permissible at sea by the usages of war.” I use the term here to mean armed formations acting in dependently of any politically organized society, in the pursuit of private interests, whether or not under the mask of the state. See Janice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22.
-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Vol. 2 , trans. and foreword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51–423.
- ^Joseph C. Miller, Way of Death: 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Angolan Slave Trade, 1730–183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especially chaps. 2 and 4.
- ^See Jakkie Cilliers and Christian Dietrich, eds., Angola’s War Economy: The Role of Oil and Diamonds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0).
- ^ See, for example, “Rapport du Groupe d’experts sur l’exploitation illégal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et autres richesses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United Nations Report No. 2/2001/357, submit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April 12, 2001. See also Richard Snyder, “Does Lootable Wealth Breed Disorder? States, Regim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trac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 See Loren B. Landau, “The Humanitarian Hangover: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Governmental Practice in Tanzania’s Refugee-Populated Areas,”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21, no. 1 (2002): 260–99, especially 281–87.
- ^ On commandement , see Achille Mbembe, On the Postcolo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chaps. 1–3.
- ^See Leisel Talley, Paul B. Spiegel, and Mona Girgis, “An Investigation of Increasing Mortality among Congolese Refugees in Lugufu Camp, Tanzania, May–June 1999,”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14, no. 4 (2001): 412–27.
- ^See Tony Hodges, Angola: From Afro-Stalinism to Petro-Diamond Capitalism (Oxford: James Currey, 2001), chap. 7; Stephen Ellis, The Mask of Anarchy: The Destruction of Liberia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an African Civil War (London: Hurst, 1999).
- ^See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 trans. C. Stewar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4), 227–80.
-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 trans. Joan Stambaug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227–56.
-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 227–56.
-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 336.
- ^ For what precedes, see Amira Hass, Drinking the Sea at Gaza: Days and Nights in a Land under Sieg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 ^Gilroy, Black Atlantic , 63.